| 在看守所 |
|---|
| http://y.sina.com.cn 2005年01月10日 18:37 新浪校园 |
|
11.在看守所 这一年的夏天,太阳很毒,没有下过一场雨。湄沁的父亲在骄阳似火的季节,黯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从路灯局传出的小道消息说,邱副厅长平生最为痛恨的两个的人,将直接或者间接地因他的离职而获得升迁的机会。他们一个是他未来的女婿酋长,另一个是善于做表面文章的上官瑞云。 酋长还在鄂西。从他的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出,他显然已经知道了自己将要获得升迁的这个喜讯。他说,从省城来的勘测队,已经完成了对水布垭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并通过了政府的立项批准。不过,他仍将留下来,一直要干到电站开工之日才会离开。他还说,水布垭太神奇了,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建造一道永久性的人工风景线,那将是造福族人子孙后代的善举,也是点燃族人理想之光、心灵之光的义举! 我给酋长回信。尊敬的酋长,我感觉我一直在被你牵引,我进入了你设计的理想王国。可是,请你原谅你的子民,我无法完成你赋予的历史重任。“路灯工程”开工以来,我又是吃官司,又是赔钱,别人的灯还没点亮,我自己的这盏灯已经熬干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整天像孙子一样,跟那些大爷们说着好话,而他们可以爱听不听。 我现在没有心情奢谈什么理想,我只想早日了结手头的事情。那时,我也许会去水布垭找你,你也可能早已返城,做着你想做的官儿。这没有关系,我还是会去水布垭,只想看看那里的自然风景和你的人工风景。我记得军训结束时,你说过四年以后我们再相见,现在时间已经过半,我希望不要错过相会的那一面,邀上湄沁、衣羊,说说我们分离后的各自感受。 我在水布垭,或者在学府餐厅等你。 写完这封电子邮件后,我乘车去了湄沁那里。我想求证路灯局的传言是否属实,还有酋长现在可以给我什么样的帮助? 当我敲开泰格公寓1幢3楼的那扇铁门时,湄沁木然地站在了我的面前,但我还是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了敌意,甚至是仇恨。我不知道她这是不是冲着我来的,我想我来的可能不是时候。 我对湄沁说:“对不起,很晚了,打扰你了!” 湄沁把我让进屋子,还是客厅那张沙发,我坐下来,接过了湄沁递上来的一杯白开水。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一句话。这让我感到了不自在,我的手在沙发的缝隙处摸索,什么也没有。 湄沁坐在客厅的地上,埋头看书,她似乎把我忘记了。 我说:“嗨,湄沁,你在看啥书呢?” 她抬起头来,盯着我,盯得我浑身发怵。接着,又埋头看书。 我站起来,走过去。她的身边,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书,从清末的《官场现形记》,到民国的《厚黑学》,再到当代的《国画》,全是官场文字!湄沁把头埋在书堆里,既不说话,也不再看我。 我大吼一声:“湄沁!你在搞什么名堂?” 她扬头脖子。“不要你管我!你走吧,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说“湄沁,你是不是还在为你父亲难过?不要这样,没人能当一辈子的官儿,总是要退下来的,一个官员的政绩不在乎他在位了多少年,而于他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我觉得你父亲就是人民的好干部!” 湄沁瞪着我,气呼呼的。 我接着说:“酋长也是一个大有希望的人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湄沁拿书砸我。“你可以滚了!你凭什么跑来幸灾乐祸?!” 我说:“我没有,我说的是真心话!” 湄沁把书扔得满天都是,她一边扔一边狂叫:“哼!乌龟八王蛋!” 她是在骂我吗?我听着不像!于是,我悄悄地退出了湄沁的屋子。在回石牌岭的路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湄沁是怎么啦?从前一个修养极好的女孩子,在一夜之间,怎么变得这么可怕?! 我趁着天黑,灰溜溜地钻进了沙奶奶的小楼。打开房门,屋里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我大声喝道:“是谁?” 沫沫扑了上来,迅速捂住了我的嘴巴。“小声点,最好不要出声!” 当我看清了是沫沫之后,我像一只泄气的皮球,瘫倒在了床上。我希望她是一个贼,最好是一个男贼,在与之交手的过程,顺便发泄一下我心中的怒气。可是,面对沫沫,我无论如何都下不了手。 沫沫凑近我的面庞,神秘兮兮地说:“毛次,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很重的事情!” 沫沫“玩失踪”和“玩重逢”习以为常了,我懒得惊奇。于是心不在焉地问:“是不是你已经完成了对我许诺的第二个心愿?” 沫沫有点不好意思。“不是,那个心愿我恐怕来不及为你实现了!” 她的故弄玄虚,在不经意中又一次勾引了我的好奇心。尽管我从来都没想过,沫沫真会给我带来什么好运。我追问的目的,也不过为了让自己在寂寞而无奈的夜晚,获得暂时的一份开心。 我佯装着急的样子。“来不及实现我也不怪你,你有这份心情我已经非常感激。告诉我,是什么心愿?” 沫沫说:“我不告诉你!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脚踏实地的,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我不愿意张扬!” “还脚踏实地?像你一样脚踏实地买彩票,默默无闻作贡献?”我不怀好意地问,“说吧,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沫沫顿了顿,她让我看到了她今生惟一的一次腼腆:“我又要走了.....” “你不是经常走吗?” “这次不同,这次是我拿到了干妈给我办理的护照和签证,我要永远地离开中国,永远地离开你.....” “那我是不是要祝贺你?” “祝贺就不必了.....”沫沫吞吞吐吐,最后问我可不可以借给她一笔钱,用于购买机票? 我说:“难道你干妈没给钱让你买机票吗?那么好吧,你可以臆造一架三叉戟出来,你乘三叉戟去新西兰好了!” 沫沫突然高声说:“你不借钱也罢,用不着损人!” 我笑着说:“我损你了吗?” 她缓和下来。“我不想和你争吵了,我想和你做爱!这是最后一次,你以后想都不可能!” 也许是沫沫想留作最后的纪念,也许是我想对她进行无聊的报复,我们做了整整一夜!沫沫的老到在于,她总能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到达兴奋的顶峰,最后又一次性地把我送入沉睡的谷底。我就像一个原始猎人,出没森林,闪跳射杀,在弹尽粮绝之后,再被一只奔跑的母鹿引诱,溺水而死,并陈尸河底。而当我被人发现时,已是世上千年! 我醒来,太阳已经爬上窗台了。我在旁边摸索,空空荡荡的,沫沫又在和我“玩失踪”。这时,沙奶奶把我的房门敲得山响。当她看见我房间已经没有了沫沫时,她大声惊叫:“昨晚,沫沫是不是来过了?她偷走了我的手链!” 上官局长志在必得。在等待上级任命的日子里,他把先前对“路灯工程”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这使我异常恼火!沫沫走后的次日下午,我赶到路灯局,与上官局长爆发了一场正面冲突。 我说:“局长大人,你能不能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整个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你这边还是无动于衷!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个了结啊?” 上官局长听见我用这种口气和他说话,大为光火。他重重地甩出一句:“你想怎么样?” 我说:“我不想怎么样,只想你按合同行事,把该拨的款拨了,如果不拨也行,那就把现有的账目算清,我们之间互不相干!” 上官局长猛拍桌子,大声吼叫:“这个路灯局是你毛次当家,还是我上官瑞云当家?你想要我拨款我就会给你拨款?!哼,你也未免太幼稚了一点吧!告诉你,这个‘路灯工程’还是我说了算!我可以叫它上马,也可以叫它下马!你毛次不是有种吗?你不是号称‘灯泡大王’吗?你可以再去告我!你再告时,我一定要送你一个‘负债大王’的称号,让你的子子孙孙都跟着你一起享用!” 上官局长的话,把我彻底激怒了。我冲上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上官瑞云,你不必这么狂妄自大,请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合作是有私下交易的。你搞烦了我,我一样可以把你和你的宝贝儿子送上法庭!” 上官局长挣脱我的手,惊诧地问:“你刚才说什么?” 我轻蔑地一笑:“你可以打电话,去问问你的宝贝儿子!” 上官局长果真拿起电话,拨通了英国的长途。当他搞清了来龙去脉之后,同样异常愤怒,对着电话筒大声叫骂了一通。然后,气急败坏地摔掉电话,再次将愤怒一股脑儿地甩向了我:“毛次,你他妈的真卑鄙!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事我一所无知!你也休想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走!你跟我一起去纪委!我们把事情说清楚,然后让那小子给你退钱!” 上官局长起身,非要拉我去纪委不可,我和他推搡起来。不知是上官局长自己没有站稳,还是我用力过猛,他一个趔趄,扑倒在办公桌上。“轰”地一声巨响,他把桌上的茶杯、文件全打翻了,纸片、瓷片散落了半个房间。旁边办公室的人迅速围了过来,有人扶起上官局长,有人朝我动了手脚。 他们要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去。那个财务处长说了一声:“好大的胆子,敢打我们的局长,送他去派出所,那是便宜了这毛贼!” 于是,更多的人一拥而上,我感觉眼前金光灿烂,浑身剧痛难忍。在一片混乱中,我听见上官局长说:“算了,别打了!大家都回去做事吧!” 我没有打算把事情闹到这一步,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一步,我仓皇逃出了上官局长的办公室。在路上,我欲哭无泪,既恨自己,又恨上官局长。思来想去,我还是期望上官局长能够妥善处理此事,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迅速改观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形势。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了上官局长的办公室,想向他道歉,或者作最后一次努力。这次,我等到上午十点,还没有见到上官局长的人影,而整个路灯局办公大楼乱哄哄的,人们都在小声惊恐地议论什么。不久,楼下响起了警车的警笛声。一群警察冲上楼来,封锁了楼道,并进入了上官局长的办公室。 一时摸不着头脑的我,很快就被警察控制起来。 昨天深夜,上官局长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乘上公寓大楼的电梯后,就再也没有走出电梯。清晨,从电梯出口流出来的一滩血水,把同楼栋上早班的人们吓了一跳,他们摁开电梯,上官局长倒在血泊之中,四肢僵硬。 上官局长被人暗杀了! 我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犯罪嫌疑人! 在看守所,轮番的讯问,让我烦躁起来。警察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对我进行三番五次的折腾:不停地演示进出电梯的动作! 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动作,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让警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干脆让我对着一部电视机,对其中的画面进行指认:“那个留着长发的人是你吗?不是你又是谁?” 这是上官局长被害时,电梯监视系统拍摄的一段录像。画面上,一个长发披肩、个子高挑的女青年面对上官局长,他们互视了几秒钟。几秒钟后,她上前一步,他就贴倒在了她的怀里。女青年再后退一步,他就一头扑倒在地上。女青年不慌不忙地打开电梯,身子一闪,屏幕一片血色。也许凶手根本没有料到这幢高楼的电梯间里,会装有这么一部针孔摄像头,或者根本就知道有这么一部针孔摄像头,而刻意进行了一番伪装。 对于警察的弱智,我感到好笑。“杀害上官瑞云的人明明是一个女的,你们为什么总抓住我不放?” “有这么身高的女的吗?那敏捷的一出手和敏捷的一闪身,为什么不是男扮女装?”警察肯定地说。 “那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 “这正是我们要问你的问题,你有同伙吗?” 我无法说服警察,那个人绝对不是我,也绝对不是沫沫。 “沫沫是什么时间离开你的?”警察问。 我说:“是上官被刺的前一天!” “她有可能去了哪里?”警察在一个劲儿地追问。 “也许在本市,也许在外地,也许去了新西兰!” 一无所获的警察,一直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看得出来,他们眼中的犯罪嫌疑人,现在又多了一个沫沫!她有作案时间,也有作案的动机,她曾说过要帮我完成第二个心愿,她可能会傻里傻气地去做傻事。可我怎么看那段电梯录像,凶手都不是沫沫!但执著的警察一定要找到沫沫!我只好告诉了他们,我惟一知道的一个手机号码。 衣羊是由张国旗开车一道来看守所的。我没有见到他们,只是听管教干部这么说,她给我送来了衣物和食物。那衣物被管教干部翻乱了,而食物则留在了看守所值班室。我不知道衣羊来这里的心情,但愿她不会相信警察的那些鬼话。张国旗为什么也要来呢?他是拗不过衣羊的威逼或者哀求?还是出于对我的怜悯与同情?当管教干部把那一堆衣物扔进监号后,我朝他大骂了一句:“你们全是他妈的饭桶!” “骂吧,你骂也没用。我们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管教干部指着我说。 他转身离去的瞬间,我遭到了同监在押人犯的一顿暴打。他们不会知道我干过武警,也不会知道一头愤怒的狮子正张着血盆大口。一番血腥的打斗,很快让我赢得了“大哥”的称号,这让我非常得意。当然,我同时还独享了那名管教干部用来制止打斗的警棍,这同样让我感到非常得意。不管怎么说,近两年的颠沛流离和毫无规则的起居作息,并没有消磨我的意志和体质。 傍晚开饭时,那个带头动手打我的人犯凑近我的跟前,将他碗中的一块肥肉拨拉到了我的碗里,并讨好地说,这是孝敬你老人家的! 我哼哼,再将碗中的肥肉拨给另外一个兄弟。他在我们这个五人监号中,年龄最小,身材最矮,是打斗时惟一没有对我动过手的人。那时,他躲在墙壁的一角,吓得脸色苍白。 “我不能坏了我们的规矩,还是大哥你吃吧!”他嗫嚅着说。 在监号,除管教干部之外,大哥享有剥夺别人吃饭睡觉的权利,也有授予别人开心快乐的权利。我让其他人每人给他拨拉一块肥肉,吃完以后,叫他再补打我一拳。因为他实在太瘦小,太没胆量了。 他还是不敢动手。于是,我鼓励他使劲,再使劲!随后,我感觉到了来自于他拳头的缠绵。后来,我换了另外一种玩法,让他们每人绘声绘色地说出自己的犯罪经历。这是做“大哥”必须掌握的基本情况,就像部队干部对士兵情况要了如指掌一样。 “打群架,那小子瓢顶开花,但肯定没死。我顶多呆上三年五载吧!” 人犯甲说。 他是带头打我的那个混蛋,也是最心虚怕死的一个。在他的被褥底下,看守所发的那本《刑法》被他翻出了毛边儿。说完上面的话,他拿出那本《刑法》,指着“伤害罪”的刑罚条款,向我讨教:“大哥,你在部队肯定学过法律,我也就这个数吧?我进来快五个月了,可以抵减刑期吗?” “如果不死人的话,你也就三至七年吧,如果死人了呢?‘啪’!” 我轻描淡写地说,并用手对着他的脑袋,比划出了一个开枪的姿势。“想当初,老子曾经亲手崩了两个像你这样的狗杂种!” “饶了我吧,大哥!”他颤动了一下。 人犯乙说:“我是冤枉的,他妈的!我还没来得及和那女的上床,警察就冲进来了,完全是一个陷阱!” 乙是一个干瘪、清瘦的中年男人,最不协调的是他凸起的小腹,那里面一定装满了胀鼓鼓的、躁动不安的精子。 人犯丙抢过话题。“我比你还冤!老子只不过是日了一下我的老婆,没想到落了一个‘婚内强奸’!有这个罪名吗?如果有,是不是每次与老婆做事之前,都要签订一份‘日×合同’?不然,哪天她翻脸不认人了,随时都会拎着一条短裤衩,去告你‘婚内强奸’!” 丁,我现在叫他“棉花”。这不仅是因为我让他打在我身上的那一拳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而且还因为他的鸡巴总是像棉条一样,从来都没有雄起的时候。他让我想起了“小公鸡”,同样是年龄一般大小的男孩子,同样是羸弱不堪的身体,荷尔蒙却有着天生的“认人为亲”,恣意制造了初级阶段的新的“贫富不均”。 “棉花”是因为参加扒窃团伙而被抓进来的。他的“干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聋哑男青年,他带领“棉花”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夏天往北方城市,冬天去南方城市,春秋在中原一带,疯狂地轮番作案。因为季节的缘故,他们要寻找衣着不多不少、不厚不薄的人群下手。因为衣服穿多了,探索起来不方便;衣服穿少了,容易被人发现。因此,他们像候鸟一样,南飞北徙。“棉花”他们每天将劳动所得,悉数上交“干爹”,“干爹”再按各人的表现,发给他们一天的生活开销,月终和年终另有一笔丰厚的奖金。 “你见过聋哑人打手机吗?坏就坏在这个手机上。” “棉花”扬起头,不甘地对我说,“‘干爹’用手机给我们发送信息,谁的口袋有钱,什么时间下手,什么时间收手,全凭他在一旁指挥。那一次,不知是他的手机没电了,还是移动公司的信号出现了故障,我在得手后,怀里的手机始终没有震动,在等待‘干爹’的下一个指令时,我被跟车的便衣抓了一个正着。‘干爹’是看着我被警察扭下车的,可我没有交代‘干爹’,是因为他还养着一帮兄弟。” 漫长寂寞的夜晚,每一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口述回忆录,仇恨的种子在心底开花发芽。最后,我总结说,这怨不得警察,相反,我们要感谢警察!没有警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在我的一番启发诱导下,甲乙丙丁深刻地剖析了犯罪的思想根源,并表示了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报效社会的决心。他们盘坐在水泥浇铸的大通铺上,群情激昂,互相抽着耳光,抽一下,说一声: “我有罪!” “我该死!” “我有罪!” “我该死!” 负责办案的警察再次提审了我。他们很有礼貌地递给我一支香烟。“请你仔细回忆一下,沫沫是什么时候有了去外国的动机的?” “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前吧,她说她的干妈在新西兰。其实,我根本就没相信过她的话,沫沫喜欢吹牛!” “你知道她还用过别的什么名字吗?” “柳蓝!”我想起了沫沫在网上骗人的把戏,脱口而出。“不过,那是一个假名!” “你还记得她的身份证号码吗?” “不知道!她根本不可能出国!” “那么,我们很遗憾地告诉你,上官瑞云被害的那天上午,真有一个叫‘柳蓝’的女子从天河机场飞往了香港,我们怀疑她就是沫沫,她很有可能转道香港去了新西兰!” “她去不去新西兰,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跟你们说过一千遍了,上官瑞云不是我杀的!”我虽然这么说,但对沫沫还是有了刮目相看的钦佩之情,如果真是她杀了上官瑞云,如果她真的去了新西兰,沫沫真不愧是一个人物! “所以,我们得让你提供沫沫的身份证号!” “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她老家的住址,你们可以去那里调查一下。”我记起了W市郊的葛店,还有沫沫那个凶神恶煞的堂婶。 几天以后,我和甲一前一后地被叫到了看守所办公室。办案警官向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结束了对你的审查,你可以离开看守所了!不过,你不得离开本市,要随时配合协助我们的工作。 回到监号,我兴奋地告诉了兄弟们这个好的消息。他们围上来,祝愿我命大福大,日后一路顺风,心想事成!日老子的,像春节拜年的祝福语,又像临终送行的悼词!只有“棉花”默不作声,蜷缩在墙壁一角,那眼神既有羡慕,也有绝望。我走过去,对他说,出来后,不要再跟“干爹”了,就跟我吧,我在外面还有一间店铺,足够养活你了! 他站起身来,抱着我哭泣。这时,甲在管教干部的押送下,耷拉着脑袋,回到了监号。像欢迎我回来一样,他们一起围了上去,询问甲是不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甲哭丧着脸说,再见了,兄弟们!管教干部告诉我说,我把那小子的脑袋砸烂了!我活不了了! 我向走廊里的管教干部大声报告,我说我不想出去,能不能再在这里呆一段时间?他说,你要是想做志愿者的话,可以去伙房义务帮厨!我说我愿意!非常愿意! 我留下来,是想陪甲,或者每天看到甲。他是孤儿,没受过更多的教育,脑子长在别人的身上,别人让他冲冲杀杀,他就一往无前,冲冲杀杀!半年前,他把别人的脑袋搬家了,也就注定要把自己的脑袋搬家!我要留下来,告诉他《刑法》是如何规定死罪的! 我的如意算盘被管教干部搅得一塌糊涂。他们根本不让我有与在押人犯接触的任何机会,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菜、切菜,将烧好了的饭菜分装在两只白铁桶里,然后由管教干部送进监号,再将带出来的空桶冲洗干净。 这里的厨师是看守所的在编职工,一个终生未娶的鳏夫。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一开始,我就和这个老男人势不两立。他从地下小作坊低价购进劣质的棉籽油,用来给在押人犯炒菜。早年看过一则科技报道,说长期食用棉籽油可能造成男性无精或死精。我认为,老男人购进的棉籽油,就是造成“棉花”阳痿不举的罪魁祸首!棉花啊棉花,正值生长期的“棉花”,就这样残酷地被老男人掐断了男根! 我偷偷地把棉籽油倒进了阴沟,但终究没有逃过老男人像狗一样灵敏的鼻子,他循着阴沟的油香味,在管教干部那里恶狠狠地告了我一状。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发现老男人炒了一盘青椒肉丝、一盘青椒斩蛋,另外还备有一小杯白酒。我想他一定是想讨好哪个值班干部,趁他看电视累了的时候,给他送去,让他美美地宵夜。于是我对厨师说,是棉籽油炒的吗?如果是棉籽油,我也去告你一状!说你想让管教干部断子绝孙!老男人明白我误会了,他冲着我恶声恶气地说,这些菜不是讨好干部的,是“送大头”的。“送大头”是号子里流行的暗语,即行刑前,为死刑犯特别订做的晚餐! 白天,有两个法医在卫生室为甲检查过身体。他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从伙房门前经过,我远远地听到了“丁当”的声音,并意外地盯看了他好一阵子。甲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不然,他肯定会叫我一声“大哥”。现在,我猜想明天的“大头”肯定是甲。我没有机会为甲送行,甚至不能对他说一声“再见”,为了表示心意,我趁老男人不注意,偷偷地往菜里淋了一些色拉油,然后,找到管教干部说,我不想干了!我要回家! 看守所建在市郊,前面有一片开阔的高粱地。在走出高墙的那一刻,我只觉大脑一阵眩晕,有好久没有见过外面的景色了。我面对雪白的墙壁,而且是架着电网的墙壁,开始撒尿!我画出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日老子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伙食差是差了一点,但精神生活也不赖,至少不像外面,没有人陪你整天说话!我在墙壁上留下了纪念。 夏末秋初,这些懒惰的市郊农民,齐刷刷地割断了高粱的脖子。他们轻而易举地取走了高粱穗子,而留下笔直笔直的秫秸,只等来日点燃一把大火,用作第二年春天的底肥。这些一茬又一茬的高粱秫秸,差不多有一人高的个头,尽管铺满了整个田野,但还是给人留下了一种肃杀、孤立的印象。我一头钻进丛林,放声大吼:嗨——!嗨——! 远处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声!我猛然一怔,突然瘫坐在地上。忽儿,我又猛然起身,抱头鼠窜,可我怎么也逃不出这高粱的茂密森林。 我听见了衣羊的喊声。在辽远的天空,她的喊声是那么悠长。衣羊一遍又一遍地叫唤我的名字,而我却不能看到她的影子。这使我激动,紧张,继而暴躁不安。 “我在这儿!是你吗?衣羊——” 我终于看到了衣羊!在高粱地的尽头,停有一部黑色的奥迪轿车。张国旗从车窗内探出一颗头来,面朝天空,长久地呆望了一片空空茫茫。而衣羊则站在轿车的一旁,执著地喊弯了身子!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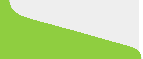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9898-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