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小世界——“A—NA—XI—DI” |
|---|
| http://y.sina.com.cn 2004年11月27日 15:54 新浪校园 |
|
孙雪晴 为一本书流泪,而且是一本厚达三百九十页的书。 我老在想,一个人安静透了,会想些什么?在一个只装满窗玻璃的空屋子里坐着,呼吸以及心跳都会使旁边的玻璃微微颤动,那时会想些什么呢?或许只一声叹息,一个世纪就悄悄地滑过去了。 一直认为看一本纯文字的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有耐性的人才去做的(我是指一口气看完)。但很意外,我做到了。 我就这样一页页地翻过去,而泪也这样慢慢滑落。我认为自己是狠狠地哭了,以至心痛的咯咯声也听得见。泪始终慢慢地淌着,不紧也不慢,我没让它滴在书上。我觉得这本写满父亲的泪的书已经够苦了。 很佩服周国平一纸的冷峻与温柔,他是怎样地叙述一个小生命从出生到毁灭的过程呵。一个一岁的小生命就这样荒谬地死去了,死得让人无法理解。如果要问缘由,大概就出在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双从光里来又回到光里去的明亮的眼睛上吧。 她只有一岁,还没有来得及在暖暖的阳光下骑漂亮的旋转木马,也来不及长大,来不及在镜子前挑选漂亮的衣服,来不及为一次小考失利而哭泣,来不及在仲夏的栀子树下等待远远跑来的他。她只在上帝刚赋予她生命的时候,来这个有光的世界走了一圈,就又被带走了。她根本来不及痛苦。记得很清楚,妞妞的父亲在书上有这样一句话:“她的笑纯净、明朗、甜美,没有一丝阴影和苦涩,纵然临近死亡,她的生命仍然新鲜。” 她的生命仍然新鲜,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稚嫩的小生命呱呱坠地时她父亲欣喜的神情,然后,她来到这个有光有声的世界,然后,她给她的父母带来无限的欢乐,然后,她被诊断为恶性肿瘤,然后,她开始了她人生的最初的成长和最初的凋零,然后,她在一辆毫无意义地驰向医院的汽车中靠在父亲怀中永远睡去。 画面像在老式的放映机中一张张晃过,由最初的炫目、明亮的光环慢慢聚成一粒极小的光点,映入我眼帘。随后,一种热热的东西又淌下来了。 我想妞妞比我坚强。她在发病时从不无缘无故地哭闹,仅在痛极了的时候小声嘀咕:“磕着了。”或许她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世界总是磕着她,磕得越来越疼。为什么有爸爸妈妈带她来这个世界还总是让她被磕着。她太疼了。她太累了。她在这有光的地方走了一圈,上帝说:“你该回来了。”但为什么来时与去时总那么叫人撕心裂肺呢?只因为她的稚嫩吗?“你们都瞎了吗?看不见最明显的事实:妞妞就是不想走!”她父亲吼着。她服了一万三千五百片安定、昏睡了十个小时,居然又醒了过来,她是真的不想走! 我不懂什么叫宿命。只知道它很强大,毫无理由地强大,它强大到可以肆意做它想做的事。它带走了妞妞,带走了那个有一双明亮眼睛的女孩。够了吗?不够。 “A—NA—XI—DI!”是妞妞一直低语的一句话(周国平称之为“神秘的隐语”)。她不哭的时候念这个,然后接着说“小世界”,一说就哭,好像很伤心,要把一辈子的眼泪全流出来。我也老想,妞妞的小世界是怎样一个忧伤的世界?那儿有别人吗?她认识那些人吗?她父亲没有说她死时的表情,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是祈求上帝留给她一个灿烂的笑容吧,她已经被硬夺走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只剩下这甜甜的微笑了。 前些天,爸爸收到一封信,说是爸爸的一个朋友患了白血病,没有多长的时间了。爸爸看信时一直不说话,只是把展开的信又端端正正地折好,然后轻轻地塞入信封。那位叔叔我也见过。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死这种东西的存在。它真的离我们很近,很近很近。仿佛一伸手就能够着。看着爸爸把信塞入信封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安静得害怕的感觉。 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生活就是生活。人的手太小了,把不住它。惊喜或者伤害,全由它倾泻而来吧!我没有勇气再重读一遍,也不想再感觉眼睛里那种因忧伤而流过脸颊的无奈。我承认自己的脆弱。“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活生生的人也总被领着,拖着,虽然抗争,但终究屈服。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者挥手甩下一卷无奈,而陪之而坐的,则是更多的无奈。 妞妞去了。带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去了。为了她,她父亲相信天上有了天堂。但愿吧。 你听到了吗,那是妞妞的声音—— A—NA—XI—DI! 写于2002年3月12日(高一)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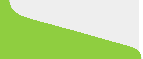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