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千年面纱下的年轻表情 |
|---|
| http://y.sina.com.cn 2004年1月19日 10:24 中国青年 |
|
漫漫一千年满壁风动。 一千年了,她们就这样飞了一千年。手中的鲜花,从来未曾落下,缥缈的身姿也从未一刻飞离这小小的洞窟。不是亲眼看到,我一直不相信简单的线条能够具有这样的律动!当手电筒微弱的光打在这些画在泥壁上的飞天时,我不由屏住了呼吸:当褚红、墨绿、浅蓝、深褐和许许多多说不出名字的颜色就这样肆意地组合在一起时,却在眼前展现出一幅极其和谐的绝美画面! 那种跃动不已的生命气息,风驰电掣的动感,遒劲飘逸的线条和异想天开的色彩,可以打动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飞天在散花、众佛在侧耳倾听、奔马在长啸、火焰在飞升……而正中的如来佛,脸上是一种奇异的微笑。一时间,一切琐小、一切浮躁、一切纷扰顿然冰解,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有什么能比坟冢内的飞翔更为残酷卓绝?有什么能比绝境中的坚守梦想更为痛苦与高洁?纵使终有一天,飞天摧折沙海沉陷,依然留在人间的神女也将依旧以其七彩瑰丽的飞翔,证明着从前、现在和未来关于梦想的故事…… 采访/本刊记者 李海波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处: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 ——季羡林 在敦煌研究院摄录部摄影师孙志军的照片里,敦煌的沙是红色的。 有红色的沙漠?他笑了,带我爬上保护所屋顶的沙坡,“你看!”晨曦刚刚在三危山顶峰出现,一会儿,一束阳光刚好打在莫高窟顶的浮沙上,果然呈现出暖暖的红色。“敦煌的美不仅仅是你看到的壁画、雕塑,还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你要用自己的内心去感觉她。” 如果自孙志军从武汉大学摄影系毕业来到敦煌算起,已经整整15年了。记不清多少个风和日丽、冰雪雨雹的日子,他就这样一寸寸地爬遍了莫高窟的每道沙梁,把沙峰驼影、野草清泉都定格在那台忠实陪伴着他的骑士相机中。 “想不想去看洞窟?”刚到敦煌的这个下午,我遇到了扛着一堆摄影器材的孙志军,正好他要去拍摄第55窟的一尊力士雕塑。就这样,他成了我在莫高窟认识的第一个人。洞窟里没有光线,需要从外边接进来一根电线,然后搬走那些立在壁画前的玻璃屏风,他轻车熟路地忙着,我想要帮忙,也不知从何下手。 “快来看看,这轮廓光特别棒!”我凑到相机取景屏前,力士的正面被一束光打亮,侧面的灯把这尊唐代雕塑的威猛神情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问,“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拍这尊雕塑?”“这是第七次了,但每一次,总是能发现一些细微的不同,能重新感觉到这些雕塑的生命力。”一边说,他一边用一根木条细心地把力士脚下的浮尘扫平。“这些照片都是要提供给相关的研究机构使用,必须尽可能地注意细节,不能因为一点的疏忽让它不完美了。” 简单地说,孙志军所在的摄录部负责把所有的洞窟用相机拍下来,让这些沉寂在黑暗中的壁画、雕塑和石窟忠实地再现。拍什么内容是研究院决定,而每一幅图片的角度、光线和拍摄方法则是他必须去解决的问题。孙志军已经在敦煌洞窟摄影中颇有建树,出版了许多精美的画册。“但这只是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作为为数不多获得“哈苏中国摄影师”资格的一位,他有更大的梦想。 到敦煌的第五天,孙志军带我沿着阳关故道造访那些已经倾塌千年的古城,所谓阳关大道,其实本无道路,孤单单一堵城关,内外大漠浩荡无涯,车马寥寥,随意而行。对于我,历史的生命就是这些至今犹存于戈壁滩的遗址,生动的历史依稀在这些世间仅存的历史空间里闪现,却无法还原。 “以前这里都是绿洲,所以才会有这些古城。”原来,几年前,他在一次对藏经洞的拍摄中想到,那些震惊世界的写本中,除了宗教和人文的意义,对于今天的敦煌,又有哪些现实的意义?从那时开始,孙志军就开始翻阅大量写本和历史典籍,他找到了许多记载文字,其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就描述了唐代时期敦煌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后,这里形成的绿洲灌溉系统,以至形成“户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四”的盛况。他决定把主题定下来——莫高窟周边环境变迁。“今天这里的大部分地方已经被戈壁和沙漠吞噬,我必须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把这种变迁记录下来!”几年下来,孙志军的目光也从莫高窟延伸到整个敦煌,烽燧、古道、草木、荒漠,一一收藏在胶片中。 当摄影已经升华为一种手段时,其艺术性和技术要求便退到了第二位。晨昏的深红色光线不再吸引孙志军的镜头,他已经把视线对准了完全真实和写实的环境记录。也许,能褪去的是照片上的红色,而内心对这片土地的赤子之心却永远保持着。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现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望我学者对内不负历劫仅存之国宝,对外襄进世界学术之将来。 ——陈寅恪 王建军的女儿两岁,在他怀里乖巧地躺着。小家伙一点儿不安分,“爸爸,我们是进城吗?你给我买什么好东西呢?” 周末是研究院员工进城采购的日子,很多人戏称为“放风”。从敦煌市区到研究院所在的莫高窟25公里,除了那些旅游纪念品的小摊,整个保护区的"商业设施"就是一家为游客服务的餐厅,所有的生活用品必须在周末通勤车去市区的时候买回来。 “我们夫妇俩都在考古所上班,平时就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说起女儿,敦煌研究院考古所的王建军脸上就有些愧疚。“其实,我们在这里至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就是苦了孩子。” 29岁的王建军已经在敦煌工作了七年,从武汉大学考古系毕业后,父母想让儿子回到内蒙古工作。"本来也想过要回去,父母年纪都大了,需要人照顾。但后来认识了彭老师。"王建军说的彭老师就是院长樊锦诗的爱人彭金章先生,彭老师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夫妻两地分居20多年。后来,敦煌北区考古开始后,彭老师干脆放弃了武汉优厚的教授待遇到了敦煌。在学校时王建军就非常敬佩彭老师的为人为学,毕业时几乎没有多想就来了。 王建军的办公室满满当当全是陶片、石块和碎布条,“可不能小看这些东西,虽说都是些局部,但一直以来学界的关注点都在南区的洞窟和壁画,认为北区是画工和僧人居住的地方,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考古,陆续在北区发现了很多有重大考古价值的材料。”说着,他拿起一块方木块儿,“这是彭老师带我们发现的木活字,从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后,从来没有发现过汉语的活字制品,当年藏经洞遭到劫难的时候,法国人伯希和带走了仅存的960枚,奥登堡劫走了130枚,彭老师在北区发现的这48枚木活字,属于国内仅有的!"讲起这些的时候,天性腼腆的王建军兴奋得像个孩子。 平时,王建军的工作就是和彭金章先生一起对一个个洞窟进行系统调查,全方位收集洞窟信息,进行内容考证,确定年代,排比分析,整体分期,完成对石窟的断代划分,这是考古学里重要的收获手段。北区的洞窟可不像南边的那些已经修好了用于游客上下的台阶,由于风化的作用,上下层洞窟之间早已没有了楼梯,必须搭梯子才能爬上去,北区大多是一些非常狭小的洞窟,没有美丽的壁画或者雕塑,只有一些残留的黑色烟道,进去后只能蹲着工作,稍不小心就会撞到窟顶。“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有,但需要时间,一点点地清理、发掘。一个发现有时候可能需要几个月。”王建军说。 “乐趣?乐趣就是发现。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心里就要有一个希望,然后,为这个希望去一点点地工作,直到开始下一个希望。敦煌就是这样,要么你什么也找不到,要么你找到一点就是特别重大的发现,这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事业,是你的骄傲。” 在这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前,我深深内疚的是,自己飘洋过海,只认这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顶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艺术却一无所知……今天,才如梦初醒! ——常书鸿 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建在一处沙梁之间,从远处看正好藏在山脊下,“这座建筑和环境融合得很好,不会对保护区的景观带来变化。”研究院保护所所长王旭东说。保护所正对面,就是历经东晋、前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明、清十几个世纪先后开凿的1000多个洞窟,它们密密麻麻排在莫高山崖壁上,上下五层,长达几公里。 12年前他刚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兰州大学毕业后,王旭东回到家乡张掖,成了一名水电工程师。1991年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莫高窟,"那时候就是好奇,想看看这里的壁画。"晚上,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几个临时工围着一台满是雪花的黑白电视津津有味看,吵得他无法入睡,干脆到外边去走走。 夜晚的莫高窟静谧安详,月光从九层楼倾泻下来,“就是那么很短的一瞬间,好像是被一种难得的大气感动吧,我当天晚上突然决定留在这里。”得知消息的樊锦诗用最快的速度为他办好了一切调动手续……“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天性喜欢大自然,喜欢平和的环境。” 王旭东在大学学的是地质专业,恰好当时研究院正为洞窟裂缝的加固犯愁,他结合自己的所学,提出“沙砾岩石窟裂隙灌浆”的方案,解决了这个直接影响洞窟安全的难题。此后,王旭东又通过对整个敦煌地区的地质环境分析,陆续完成了“莫高窟地区断裂活动特征和对石窟的影响”等重大课题。 “作为已然存在了千年的古迹,莫高窟每一天都在面临最严峻的保护难题。”身为保护所所长,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要实现科学保护,就要先弄明白石窟病害机理以及进行壁画修复技术研究,从宏观到微观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保护系统。 单就裂缝而言,就属于文物保护中极难应对的病害。裂缝是来自地质本身的病害,这里的地质属于沙砾岩,由小鹅卵石,沙土和钙质物胶结而成,这种松软的沙砾岩很容易风化,浸湿后还会脱落,王旭东和保护所研究人员制定了一套方案,首先把地下水控制住,然后采用锚索技术固定松裂的岩体,对于岩壁的裂缝和孔隙进行灌浆封闭,使之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 接踵而来的是壁画的病害。壁画那一层薄薄的表面布满了艺术家的感觉神经,它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哪怕是色彩最微妙的变化,线条最少许的走样,也会使画面的情感与力度全然不同,魅力便会陡然失去。千年的岁月,大自然的风吹沙浸,日晒雨淋,加上人为的破坏,烟熏火燎,各种各样的病害侵入到壁画中。其中起甲和酥碱是最难治疗和危害最大的病害,经过多年的试验,终于,他们发明了一种“针头注入修复法”:先用吹气球、羊毛笔等将起甲和酥碱处的尘土和积沙清理干净,进而用注射针筒注入一种用聚酸乙烯和聚乙烯醇配制的粘合剂,再用白绸按压壁画使其粘牢,最后用小木棍滚动轧平。最后上一层无色透明、不反光的保护液。 “听过敦煌古乐吗?”王旭东问,我摇摇头,他拿出一个装帧精美的木盒,里面是两盒普通的磁带。“这部古乐是从敦煌遗书中整理出来的,1994年曾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这部世界上最古老的乐谱被翻译出来后,很多音乐家称之'人间仙乐'。" 曲调突然急剧变化:荒沙如雪,寒月如霜,塞外的冷寂、征戍的艰辛从弦音中透出来,插入琵琶的弹奏:忽而细雨,忽而滴泉,虽短犹续……我们沉浸在这绝美的音乐中很久。 “单一个曲谱,就能有这样的成就,更何况其他!敦煌壁画是历代民间艺术家的心血,仅现存的400多个洞窟壁画而言,以一平方米为单位,能连接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我自己不是艺术家,但我明白这些艺术品的巨大价值,它们是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留给人类的珍宝!" “我们每一分钟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前人的创造留给后人。如果,让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损失一分一毫,那是真的要背上‘千古罪人’的骂名!”王旭东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信和骄傲地说。 面对敦煌文明,任何一个学者都会感觉得到它的浩大无边,也会感到每一个具体学科的深不见底!就像一个世界那样,敦煌充满了未知的空白和无穷的神秘,对于它,我们已知的永远是远远小于未知…… ——冯骥才 魏丹想把几根从戈壁滩里拔回来的芦苇摆在宿舍墙角,可它们实在太高了——最短的一根也足足有3米,她站在那里犹豫是不是要把它们剪短。 小小的宿舍里,摆满了四处收集来的“宝贝”:看起来没什么不同的几块石头、一些瓦片(据说是从长城废墟上捡到的)、养在大鱼缸里的两条很丑的鱼,还有,贴了满墙壁的照片。“这张是我们去爬三危山,五个小时呢,累得腿都快断了!看这张,是一个周末徒步‘穿越’鸣沙山脉,好几十公里呢,在沙漠里从早上走到中午,还有这张,去五个庙……”她兴冲冲地列举着自己的“壮举”。 这么说,你可别以为她真的就是一个贪玩儿的小女孩。第一天到敦煌,打电话给她,魏丹一脸公事公办的严肃,安排采访对象和日程有条不紊,那股利索和成熟的劲头让我一时不敢相信她和我一般年纪……从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院,魏丹已经当了四年的院长秘书了,要真板起脸来,就连平时一起关系最好的小路也怕她几分呢。 不过小路现在可不怕她,“院长出差了!”魏丹开心地一蹦老高,偷偷捂住嘴巴,“可不敢这么大声。”这段时间是研究院一年一度的总结工作阶段,院长每天忙到凌晨,她做秘书自然也没什么机会“偷懒”,从早忙到晚,“特像一个小陀螺。”魏丹这样形容自己。 研究院里年轻人很多,周末相约一起去爬山、野炊、进城大吃特吃,都是让魏丹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这个周末我决定关掉手机!”她想了想,“其实关不关都没信号……对吧,孙老师?”原来,听说我们打算去敦煌周边“考察”丝绸古道和玉门关,她就缠着孙志军一定要带上她一起去。 第二天清晨出发时,天还没有完全亮,车灯照到的地方是细细的黄沙与沙砾混合的戈壁滩。几个小时过去,全然没有人烟迹象。戈壁那么宽、那么长,肆无忌惮地往远处伸展,根本没有尽头,无论往哪一边看,除了戈壁还是戈壁,视线中惟有天空和戈壁滩,人和车都被苍凉的颜色覆盖了。 在城市里久违了这么闪亮的星空,以及,星空下黄得纯粹、黄得彻底的土地。 路边到处可以看见倾塌的荒城,被黄沙和红柳埋没的村落,以及几乎消没于地面的汉长城,两千年前的烽燧墩,残破败落,却依旧一个个兀自耸立在大漠上,黑黑的历史阴影躺在它们身旁,那些用于燃放烽火的积薪历经十余个朝代,犹然完好地遗存。 沙漠的黄土将历史所遗弃的事物轻轻地掩埋起来,楼兰、尼雅、且末、若羌、高昌这些曾经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城池,如今都化为倾塌的泥屋和晒成了白色的胡杨干枯的树干,半埋在沙砾中,被流沙一点点地堆积和掩埋。 “真想留在这里,放一群羊……”临近河仓城的一处戈壁上,一个孩子赶着一群羊从车旁经过时,忽然听见魏丹这样说,大家都笑了,“那你得首先嫁给一个放羊娃才行!”孙志军开玩笑地说。 傍晚,在回到敦煌的路上,魏丹不停地看手机,“今天一天没信号,老太太不知道急成什么样了……”她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工作。“老太太”就是樊锦诗院长,私底下大家都这么亲切地称呼这个一工作起来就什么都忘了的领导。“说真的,秘书这个工作本来就很庞杂,再加上老太太又把敦煌的事业当自己的命一样,不辛苦才怪了。每天到凌晨,回到宿舍就光想着怎么能快点把自己扔到床上去,早上6点起来继续......你不会觉得我的生活太简单了吧?" 在敦煌采访的20多天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跟我"又恨又爱"地提起"老太太",恨的是她几近于苛刻的工作要求,常常因为工作的进度被她毫不留情地责备......爱的是老太太那种对敦煌毫无保留的痴情和赤诚,60多岁的老人身形瘦小,却要和大家一起担起日渐黯淡的壁画带来的巨大压力。"有时候到深夜,我觉得自己这个年轻人都已经熬不住了,可老太太冲一包方便面,又开始忙上了......我哪里好意思去休息呢。不过,跟着樊院长做事情特别有激情!和她接触,你就能发现那种学者特有的执拗、率真和严谨。" 也许因为专业是考古的缘故,樊锦诗说她对敦煌艺术的了解有限,那是什么在支撑着她一个上海女子在西北大漠里一待就是40多年呢?从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到如今满头银霜,值得吗?我曾听过樊锦诗一次对大学生的讲座,当她谈起敦煌的历史文化价值时,那种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疼爱和骄傲溢于言表。但这种挚爱的代价却是夫妻20多年的分居和几乎被吞噬的健康啊...... “我刚刚给老太太做秘书的时候也不理解,后来有一次,邵逸夫先生为敦煌捐款,他说了一句话:对我而言,捐款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对你们而言,现在所做的一切,可能要50年后才有人理解......我想,如果不是樊院长他们这些人今天去做保护敦煌这样的事情,等到50年后,一切就为时已晚。" 这里和云冈、龙门石窟雕刻一样,其气势之雄伟、造型之生动,使我体味到中国艺术的“气韵生动”四个字。南齐谢赫的“画有六法”是当时评定中国画创作的标准,想不到在敦煌壁画中得到了印证。 ——周恩来 “壁画中最美的部分就是表情,因为所有的表情都是心灵的语言,你看,这些虔诚的、平和的、庄重的、闲适的、愤怒的、紧张的、快乐的、满足的、期盼的、傲慢的、依恋的、狂妄的、善良的……”韩卫盟在画夹上一边临摹壁画一边说。 韩卫盟、范丽娟,美术部最年轻的员工。这两个刚刚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完全沉浸在这个佛国的艺术世界。“但我们在学校学的是油画,油画和敦煌壁画的线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范畴,所以,先要用一年的时间熟悉线条的运用。” 壁画临摹首要的要求就是“原样复制”,这种具有学术性的临摹需要高超的绘画技巧,而线描在技巧中是第一位的。作为中国画的根本,线描体现的不仅仅是轮廓,更是精神的形体与形态,如何做到精确又爽利、流畅又老到、清纯又优美、严谨又自如——就像这些千年的壁画,把线描的表现力发挥到一种极致,这是韩卫盟和美术部的工作人员力图去掌握的。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一批批奔赴敦煌的人中,大多是画家,从张大千到常书鸿、段文杰,敦煌首先是作为一条沙漠上的大画廊,一个千年的绘画史博物馆,一座世界上最浩大的美术宫殿展现。而最直接被这里震撼的也首先是画家,很多画家喜欢这样说:“没有去过敦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绘画史。” 259窟,这尊禅定佛的微笑传达出一种慈爱和超然,几笔之间就勾勒出人世间最迷人的微笑,这是惟东方艺术才具有的极度抽象和隽永的含蓄美,"以形写神"的传统审美精神在这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凸现。 在城市长大的韩卫盟和范丽娟刚刚到这里的时候,还真有些不习惯,莫高窟的生活相对要简单很多,“起初,下班后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从宿舍到洞窟,从洞窟到宿舍,生活被浓缩为一条直线。 斑斑驳驳的剥落痕迹、微小的裂缝孔隙、沉黯幽深的变质颜色,都要分毫不差地复制出来……他也曾怀疑过这种“机械”的复制到底算不算自己的艺术梦想…… 喜欢毫无顾忌地大笑的韩卫盟进了洞窟后格外地严肃,“壁画临摹就不仅仅是在学校学到的那些技法能够涵盖的了,美术部很多特别出色的艺术家,他们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就是临摹壁画。” 韩卫盟带我去看他最喜欢的一幅临摹作品。这幅《都督夫人礼佛图》是前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的作品,和洞窟里经历了漫长岁月侵蚀、模糊难辨的原图不同的是这幅作品无论从构图、颜色和动态以及笔墨的线条上,都充盈着一股神秘和华贵的盛唐气质! “段先生给我们这些临摹工作者曾定下了三条规定:客观忠实再现,不能随意删改;重在传神,突出整体神韵;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这三条相当苛刻,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临摹传达出原作品的精华。”已经退休的段文杰是韩卫盟最为敬佩的老艺术家,当年也是像他这么大时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而来到这大漠里,一待50年...... “其实我们的工作,除了传播一种美,同时也是在发现的过程。进到洞窟你会觉得是一代代的艺术家在展示自己最出色的一面,而每个壁画背后又牵连着复杂的社会环境。想想看,单从这里撷取的一个飞天舞姿,就能引起全国狂热,当年张大千从这里仅仅‘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那么这4万多米的壁画又有多深的蕴藏......那还不也得一辈子待在这里!"韩卫盟看了看身边的女朋友,两人相对而笑。 千佛洞在世界上罕见,但那里是沙漠,与城市隔绝,其艰苦异常,若非没有事业心到那里,一定干不久也干不长。 ——于右任 从敦煌研究院宿舍出来,沿着一条沙梁前行,夜色中大地静寂,如果不是风吹动红柳的一点声音,整个世界就没有了任何声响。 沿着小路一直往前走,一排墓碑出现在眼前,那是已经故去的莫高人静静地躺卧在这里。从这片山坡上看去,整个窟区一览无余,活着的时候他们是莫高窟的守护神;故去了,他们仍舍不得这片土地,在另一个世界从这片山坡守望敦煌……他们中很多人是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离开人世的。我轻轻拨开盖在墓碑上的浮沙,借着电筒微弱的光,一个个看过去: 常书鸿:1904年~1994年,浙江杭州人,早期与徐悲鸿等留法,至今法国博物馆收藏其早期油画作品,1936年回国后到敦煌,历尽千辛万苦一生致力保护研究敦煌,被世人称为"敦煌保护神"...... 李仁章:山东文登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教师,1932年~1964年。代表作:人民大会堂青海厅群雕。1964年秋天,年轻的鲁美教师来到敦煌,在这个艺术的海洋沉醉,如饥似渴地临摹着精美绝伦的壁画,当有一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看到壁上的飞天,年轻的艺术家被惊呆了,他忘了自己站在数十米高的地方...... 毕可:1920年~1960年,这位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当年主动要求到敦煌工作,然而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艺术家被送到了夹皮沟农场,一年后饿死在那里......这座墓里面没有遗体,同伴们把一包夹皮沟的黄土葬在三危山下,每一年,他的学生们都会来这里,给他的墓碑前放上一颗红色的石子...... 窦占彪:1917年~1990年,不认识一个字的泥瓦匠,在敦煌整整48年,莫高窟492个洞子,每一个都有他亲手修补的痕迹,这里的每一条栈道、每一级台阶都是他一块砖一块瓦修起来...... 赵友贤、李复、龙时英、潘玉闪、许安、吴小弟…… 这里的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每一个灵魂都为这座神圣的艺术宫殿增添着光彩。远处,大泉河对岸,北区的山上有许多蜂房一样狭小的洞窟,那是当年绘制敦煌壁画的画工们居住的地方,很多人病了、老了、伤了,就默默无闻死在那里,连一张盖在身上的席子也没有,千百年的风沙吹进洞子,尸骨也慢慢被掩埋。 也许,那些千年的画工们也和这些人一样,在敦煌的土地上孤单地游荡,默默地守护着这座世界上最大的画廊。 夜深了,天却更蓝,大而明亮的星星形成的银河缀在天幕,抬起头时,不经意间可以看得见流星划过天际,只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悬挂在九层楼大佛殿的18只铁马风铃在风中"当啷当啷"的声音一下连着一下,传到很远,悠远苍凉。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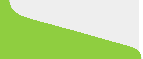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