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壶、茶垢与复旦精神 |
|---|
| http://y.sina.com.cn 2005年09月20日 21:09 复旦百年校庆网站 |
|
我们受惠于复旦,也都贡献于复旦,我们来到复旦,终又离开复旦,正如佛家所言“业”的流转。复旦是历史上的和今天的复旦人造作而成的“共业”。共业之“共”,共在何处?这就是要讨论“复旦精神”。 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讨论,我们大家不知不觉地就在这个共业中,犹如本来就是存泡在一把积了百年茶垢的老茶壶里的茶水,自然地就有了特别属于这茶壶的味道。此刻要这茶水自己来说一说自己究竟是什么味道,那是很难的。 不过,还应看到,茶壶与茶水的比喻并不完全合适,毕竟,我们都是些能跑、能看、能思想的“茶水”,我们还能跑到别的茶壶中去呆上一阵子。回过头来,再回到原来的这把茶壶中,即会感受到自己原来就是这把“ 复旦茶壶”中的水,并且同时又能感受到作为复旦的茶水,好味道是什么,不太好的怪味道又是什么。若把上面比喻的说法再引伸一下,则可以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上去,那就是“茶水”跑动得特别勤快,有的“茶水”还不是从茶壶中来的,或许竟是从玻璃杯乃至洋酒杯里来的。这一切对于一把老茶壶来说确实构成了一个考验,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考验:它日久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地是一把茶壶? 假如从这个茶壶中进进出出的水,渐次地不再是茶水,而是淡水或别的什么水,你怎么能指望它在出去之前留下什么“茶垢”呢?它的“贡献”恐怕只能是做“减法”了,除了给这茶壶加进一点子异味、带走一点子茶垢之外,别无其他。 面对这一可能的前景,我们在心态上可以有两种选择:其一,何必执着于做“茶壶”?茶壶不就是器皿吗,只要能存放水或其他什么液体就行了。君不见,科学与市场经济时代以效率为目标?而效率总与普适性相关,你讲求个性,实在是落伍之见。其二,不要怕“异味”,而且味道越杂越好,那叫“多元化”。 这两种选择,立足点不一样,结果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茶壶不再成其为茶壶,所以,归根到底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这种选择若能让大家都心安,倒也罢了,所谓“复旦精神”之讨论也就实属多余。 不过,实际说来是心安不了的。你看今日之复旦,固然已有种种日新月异之处,但却还是一把老茶壶,大家都还珍惜着这把茶壶,这是有证据在的。 你看复旦每晚的各色讲座,教室里人头攒动,演讲者与听众交流着对于时代突出问题的不同见解。 你看复旦的讲课,总是不断地有来自外校的“蹭课者”,他们逃了本校的课,或在单位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来听复旦的“高头讲章”。 你看复旦的丰富多样的学生社团,理科的偏要研讨、辩论人文的话题,文科的偏要考察自然科学的前提与前景。 你看复旦学生对教师的“苛刻要求”:不能照本宣科,不能以权威自居,不能不让学生发表不同观点。 你看复旦学生的自办刊物,其话题有时大得惊人,只有大师级的思想家才敢问津。 从这些现象中,我们自然地嗅到了一把老茶壶中的独特茶味。茶味自然首先来自茶叶本身。复旦本科生源的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茶味之独特,则不能不归诸茶壶,不能不归诸茶壶中的茶垢所造成的泡茶叶的那个水的环境,不能不归诸茶垢中的“茶精”。 上述这些至今留存着的复旦现象,绝非凭空而来。它来自传统。 传统为何物?传统不是单纯的过去,不是对过去的单纯的记忆。 传统是活在当下的过去,是在当下存在着、并且筹划着将来的过去的力量。茶垢中的茶精就是这种力量,它一方面让茶壶保持其为茶壶,另一方面又迎接着每一份新茶水的到来,从中继续生长自身,这样,它就是一个日日新的老茶壶,而绝不会下降为一个一般的器皿。这就是茶精之可贵。 我们中国的大学会不会有朝一日都成了“玻璃器皿”,就要看那些“老茶壶们”能不能自存于由随时可替换的一大批玻璃器皿所构成的当代世界中。 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复旦精神”的缘故。 ■王德峰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哲学博士)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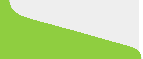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