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偶记(图) |
|---|
| http://y.sina.com.cn 2005年09月07日 18:56 《青年文学·下半月版》 |
 图/郭晓笛 文/流水剑客 这是个遥远的小镇,有一条护城河,河边是个古老的木制看台,站在看台上,就可以隐约看见远处一座矮矮的山。 这也是个被遗忘的小镇,居民寥寥无几。根据书中的记载,几年前的一场灾难让这里变得荒凉了,但荒凉使得河水更加清澈。你可以清楚地看见一种类似长脚蜘蛛的水虫,在水面上悠然地滑过,掠出一圈圈美丽的水痕。 一家面馆,一个用粗陋水泥浇灌的旅馆,大约十几家住户,就是这个小镇的全部。面馆是一个流浪的人在此歇脚时开的,它带来了北方咖喱的香味。那个年轻世故的小伙子让这个小镇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都是热气腾腾的。旅馆是这个小镇曾经惟一的富人留下的遗产,她的女儿在十六岁时成了最美丽的女老板。 传说中,这个旅馆里有一个让人议论纷纷的房客。人们说他是个怪物,他的身体里一直留着几枚子弹和手榴弹的弹片,有人曾清楚地听见他在凌晨的时候浑身发出吱噶的响声穿过小镇的街道,一直走到小河尽头的木制看台上去。 但是在传说里没有一个狙击手。几年前,当这里还是硝烟弥漫的时候,从那座看台上可以看见的山里有一个狙击手,他的子弹能够阻挡每一个方向来的敌人,但是在最终的胜利后,他的名字渐渐隐没在了小镇的宁静里。 很多年前,人们亲切地叫我小木。后来,那些亲切的人大多都阵亡了,或者因为伤后的病痛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有个父亲,没有母亲。 因为,我是一个木偶。 我的一切,是我的父亲用木头和战场上那些废弃的螺丝零件拼凑而成的。他们说,我将会是个男人,可是我不相信,虽然我穿上了衣服,虽然我开始和他们一样拿起了枪,但是我明白我的胯下始终只有一颗用来固定的螺丝,而且容易生锈。我不是男人。 学会作战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我还是个战争的天才。因为,敌人的子弹可以洞穿我的胸膛,但是,我没有心脏。 我的动力源自我父亲的死。他一死,我的四肢就能够活动了。我名正言顺地扛起了父亲的枪。 我和我的战友们打的是保卫战。我常常拿着重机枪冲在最前面,吸引敌人的火力。那些强劲的子弹穿透我的身体,留下了一个个孔。在每次浴血奋战的时候,夕阳的光都会从我的背后透过那些子弹孔穿过来,在我修长的影子上留下不规则的亮点。我想,那真是美极了。 战友们开始担忧我的身体,因为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变成一堆废弃的木头。因此他们给了我一把狙击枪,把我的位置安排在了高山上。 我成了当时有名的狙击手。因为我的手没有脉搏,不会颤抖,所以我的精确度达到了九成九。我不知道疲倦。我的精神永远保持清醒。我可以坚持一个月,用九百颗子弹,准确击中八百多个目标,但是超过一个月就不行了。狙击枪的后坐力以及山中的湿气会让我的躯体破碎、腐烂,于是,他们就给我多加螺丝,擦一些擦枪用的黑油。 他们说,我是个没有神经的木偶,不会知道疼痛是什么。本来我想说的,可是我还是忍住了没说出来——疼痛。是的,当那些山里的蚂蚁啃咬我的躯体,当那些生锈的螺丝因为肢体的运动而发出痛苦的响声,当那些遗留在身体里的弹片因为天气闷热而膨胀扭曲时,我真想有辆坦克能将我轧成碎片,那样或许会好受些。 我的脸上没有表情,所以我不说,他们就不会知道那些疼痛。 保卫战持续了很久。我们与后方的联系早在两个多月前就断了。后来听说我们被后方遗弃了,再后来我们得到了确切消息:后方被消灭了。我们是被遗弃的部队。 我们渐渐变得麻木。我的战友们开始觉得战争其实就是生活,但是灾难紧接着就来了。从天而降的白光,让我感到一阵将要被熔化的热。我看见我的战友们一个个僵硬了,脸上泛起很大的水疱,我轻轻用手一戳,就破了,里面滚出沸腾的液体,慢慢变成一条条凝固的血条。 他们死了。 我的周围死一般寂静。那些绿色的树耷拉下了脑袋,叶子在第二天就枯黄了。鸟儿们一只只掉在了地上。它们渐渐腐烂,剩下细小的骨架,一踩就碎了。 我爬上山头,回头望我们所保卫的小镇。那里已成了废墟。那些废墟里的钢筋水泥不规则地排列着。烟雾从很多处废墟中升起,夕阳从废墟的后面透过一些缝隙艰难地射入我的眼睛,那也真是美极了。 夜晚,我将战友们葬在山上。因为找不到活的树木,所以我搬了几块大石头,堆砌在他们的墓前。 然后,我继续埋伏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天又一天。我学会了用擦枪的油润滑自己的关节,虽然我的手坚硬得很难弯曲,但是办法总会有的,有些新长出来的嫩竹枝不但可以很轻松地完成我想做的事,而且可以帮我清理出那些我的身体内风尘的沉积物。 周围渐渐有了鸟,他们是从哪里飞回来的呢?有只鸟还停在了我的头上,看到我不动,它就在我的头上拉了一堆软软的鸟粪。我不能动,战争的经验告诉我,这是作为一个狙击手最基本的条件。 但是很巧的是,这堆鸟粪里有一颗从远方带来的种子,它在我的头上发了芽,长出了一株嫩嫩绿绿的草。若不是因为头疼,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非常怨恨地拔下它,又非常虔诚地把它种在了战友的墓前。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小草发芽了,春天就应该来了。 我想起战友们曾经总说,等春天到了,我们就胜利了,战争也就结束了,刚好擦枪的油也快用光了,这个消息真让我高兴。我决定到城里去,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我叫小木,我是个狙击手,我要告诉你们,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这真是一件让每个人都高兴的事情。 风吹过废墟,从那些长满青苔的缝隙里发出丝丝的声音,高低不同,长短不一,好像是有人呜咽,也好像我的父亲在世时,用竹管子吹出来的婉转的曲子。 大地龟裂的痕迹被我踩在脚底。那些蜿蜒曲折的创伤让我以为有东西在里面一直拼命地蠕动着,想要挣脱出来,拔地而起。可以看到有人的骨架斜斜依在倒塌的墙壁上,他抬着的手刚好被水泥块架住,食指的骨头弯曲着,仿佛对远处即将来临的希望充满期待,但是远处什么也没有,空旷宁静。天空中白色的云,厚得令人窒息。 一切似乎都已经改变。这里没有人烟,让我失望。我自以为的胜利信念变得脆弱了。 只有河水依旧流淌着,它从远处带来了生命:一簇水草,一群蝌蚪,一只可以在水面游动的八脚虫。河流那头的看台稍有些歪斜,但是却执拗地支撑着。战友们说,镇里的人们常常会在这里载歌载舞,山上的那些战士,可以依稀看见姑娘们的花衣裳。 现在的看台却只剩下了凄凉,但就在这凄凉的光景里,我突然看见一个穿花衣裳的姑娘。在这个灰色世界里,那是惟一的色彩。她正以翩翩的姿态,落入那条河中。我有很好的视力,我看见了她眼睛里的绝望。 那条小河水流湍急,虽然不是很深,但也足够让一千个这样穿着花衣裳的姑娘死去。我不是很懂得游泳,但是我用不着呼吸,而且,我是木头做的,天生就可以浮在水面上。因此我决定去救她。 她向水底沉去,双手无力地摊着,痛苦让她时而扭动一下修长的脖子,时而抽搐地蹬一蹬脚。我拉住了她的手,一用力,就把她放在了我的身上。她浮出水面,我划动另一只手臂,向岸边游去。 我的脸浸在水里,从水下望着天空,那是一片支离破碎的蓝色,让我不安。水很凉,我感觉它流入了我的关节,甚至从我身上的伤口渗透到身体里去了,这使我行动很不顺畅。我身体里残余的油漂浮在水面上,五颜六色的,像飞快地开放的花朵。 姑娘安静地躺在阳光下。我望着她。她的睫毛很长,鼻子小巧得让我有种想摸一摸的欲望。这欲望持续了很久,但是我不敢动她。我的身体坚硬,她的身体却如此柔软。刚才救她上岸的时候,我已经把她的手捏得红肿了,我怕再把她弄疼了。 她咳嗽着醒来,吐出带着血丝的水,这使她苍白的嘴唇变得红润了。我坐在蓝天白云下,非常开心地看着她睁开了眼睛。 她说:“你把我的手弄疼了。” 我说话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的声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声音听上去冷硬机械:“我不知道你的身体这么柔软。” 她说:“你为什么救我呢?我的生命难道是能够拯救的吗?” 我说:“战争胜利了。春天来了。山林里那么多的人,为了你们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姑娘仰起脸,望着远处的山林,眼睛灰蒙蒙的。她问我:“胜利了么?所有的人都死了,为什么你没有死呢?” 我站起来。那些水起了作用,我的身体像是快倒塌似的吱嘎作响。我回答她说:“你看啊,我是个木偶。”我努力地想摆几个造型,让她看清楚些,而一切似乎都力不从心,我倒下了。我的关节被水腐蚀了,它们锈在一起,我听见水在身体里的声音,那是即将腐烂的声音。 姑娘虚弱地站了起来,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当我倒下的时候,夕阳的光芒从我身体上那些子弹孔里透射过来,那种美,一定让她目瞪口呆了。 姑娘有一家旅馆,那是小镇上为数不多的保存良好的建筑之一。灾难降临的时候,姑娘正在旅馆的地窖里拿酒,所以她侥幸躲过了那次浩劫。但是那白光似乎能渗透到地下去,她还是被灼伤了。她走了很远的路去城里看医生,得到的答案是,她最多只有半年的寿命,而且在这半年内,她的眼睛会一点点看不见东西,头发会一根根掉光,身体也会一天天急剧地苍老下去。 她在帮我处理那些腐烂的伤口时,告诉了我这些事情。我躺在她的旅馆里,她先用酒精擦洗我身上的污垢。那些刺激的液体让我的伤口疼痛得非常厉害。我睁着眼睛,一动不动,看着那些从我身体里渗透出来的白色泡泡。 她说:“酒精能消毒,那些伤口就不会腐烂了。等会儿我再帮你涂些缝纫机用的机油,你就可以自由行走了。” 她又说:“如果你是人,肯定会疼得受不了,还好你是木头,没有疼痛的神经。” 我突然就有一阵冲动,我告诉她:“其实我知道疼痛,只是习惯了,并且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是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就像这以后,当我爱上了她却不知道怎么告诉她一样。 她沉思着,眉头皱了起来:“有些疼痛真是比死亡还痛苦,你又何必救我呢?” 我说:“要死也要开开心心去死吧,你这么美丽。” 她笑了,嘴角弯弯的,挤出了两个酒窝。她说:“我的美丽即将不在了,为什么不让我美丽地死去呢?” 我说不出话来,怔怔地看着她脸上的酒窝。我想我若是笑了,估计只会挤出些木屑。 她又咳嗽了,用手帕擦去嘴边的水痕,喘息着说:“我饿了。” 我于是真的笑了,我脸上的那些木头吱吱嘎嘎地响起来。我舒展开手指,说:“我去弄吃的,我会做拉面,即便是死,也要吃得饱饱,开开心心地死去吧。” 拉面,那是我学会做的惟一一种食物。面粉、水、再加上调料,和在一起就可以做了。我的手指均匀,所以拉出来的的面条也粗细均匀。过去在山林里的时候,他们都爱吃我做的拉面,他们说那面条有股楠木的清香,而楠木,就是做成我的手指的木头。 他们不让我干其它生火做饭炒菜之类的活儿,他们怕我切菜的时候把手指一起切了进去,怕我生火的时候把自己也烧成了灰烬。 拉面填饱了姑娘的肚子,于是姑娘开始缓慢地说起她的故事。 姑娘的名字叫小路。很多年前一个男人在这条小路上认识了她的母亲,那时候那个美丽的女人开着一家旅馆。男人出现了又消失了,十个月后小路降生了。母亲望着父亲离开的方向给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小路。在小路十六岁时,母亲终于幽怨地死去了。旅店是她惟一的遗产,于是小路成了小镇上最年轻漂亮的女老板。每个年轻的男人经过这里时,都会和她开玩笑说:“小路,今天我要到你家去开房…… ” 小路对我说:“那些年轻的男人都死了,连同我的心上人。小镇再也没有年轻的男人来了,我只会孤独地死去。” 我说:“不,会有年轻的男人来这里的,会有男人爱上你,你会开心地死去。”我当时不懂得修饰,“你会开心地死去。”类似这样的话语,不会让任何人开心。 小路凄婉地笑着说:“你是男人么,你会爱上我么?” 我是男人么?我只有一颗类似男人的螺丝,更没有男人的冲动,只有冷静。木头和战争给予了我别人不可能拥有的冷静。我仰着脸,认真地对她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男人,但是今天,我要到你家去开房。” 小路的眉头舒展开来。她咯咯地笑着说:“我不收你的钱。” 于是,我成了小镇上的第一位客人。 那个春天我陪着小路看了很多电影。小路把一个名叫《Titanic》的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很奇怪,那部电影让小路伤心了,流泪了,但是她为什么还要重复看这么多次呢? 她对我说:“假如你是个男人该多好啊,那么潮水来了,他就不会死了。” 我明白,善良的人看另外一群善良人的故事,总希望有个美满的结局,于是我说:“那个男人又不是我这样的木偶脑袋,他干嘛不绑个救生圈在身上呢?” 我不怎么需要休息,因此晚上的时间我都用来看书。小镇上有个荒废的图书馆,我把那里的书成箱地搬回来,一本本地阅读,虽然是一目十行,但是在我那个木头脑袋里,那些字就像刀刻的一样,看完了就会铭记在心。我甚至可以将书上的内容倒背如流。 我知道了这个镇子之外还有很多城市,知道了山外还有很多山,也读到了一个鼻子会长长的木偶的故事。那本故事书里的木偶,被定义为一个善良的人。他的结局那么好。我想,这么呆的人都会有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小路不能有呢? 我还因为那些书而开始崇拜英雄了,开始羡慕吟游诗人的浪漫,明白了有时候骗子也是好人,也在恍惚间懂得了爱。 一个木偶会有爱么?我爱我的父亲,但是他在战争中死去了;我发现我也爱上了小路,只是上天已经决定,她将在不久后死去。 没有人会有永恒的生命,做成我的躯体的木头也会在若干年后腐烂。我在读书的过程中,似乎恍然明白了一些关于人生的道理。 小路有把精致的梳子,琥珀色的。她很喜欢早晨拿着这把梳子梳头。她长长的黑亮的头发在梳子的齿间泻下。小路还有面镜子,她梳头时就是照着这面镜子的,那是她满十六岁时母亲送给她的礼物。她的母亲说:“一面明亮的镜子,可以让一个女孩也明亮起来。” 每天早上小路梳头发时我都会在旁边看着,小路对我说,她喜欢有人看她梳头。 那天有风,阳光很好,废墟里已经隐隐约约地长出了许多绿色。小路的脸蛋,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红润的,但是那天,小路拿着漂亮的梳子忽然呆住了。她本该红润的脸蛋变得苍白。我看见梳子上满是脱落的头发。那些头发飘落下来,无声地落在地上。 我是个木偶,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头发,只是在很久以前我的脑袋上曾长出过一根小草,但是,我还是隐约地明白了脱落的头发带给小路的悲伤。 小路没有说话。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一直等到她把精致的梳子放进了梳妆盒,我才鼓起勇气慢慢地对她说:“小路,你真漂亮。”这本来是我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安慰小路的话,但是我却看见泪水顺着小路的脸颊滑下来。 那天晚上我照旧做了拉面,这使得整个旅馆都香喷喷的,带着楠木的味道。小路曾经笑着跟我说,她总抵不住这简单的诱惑。但是这个晚上,小路并没有出来吃我的拉面。她的房间里点满了蜡烛,她哭泣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整个小镇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我还知道,她的房间里点满了蜡烛,但是她的眼睛里却只有一片模糊的白光。 第二天晚上,小镇上来了第二个客人。 我站在门外,对小路说:“那个人有一双惺忪忧郁的眼睛,他的头发散乱地垂着,一只手老是缩在袖管里,另一只手握着把口琴。他吹的曲子有时呜咽,有时欢欣。他像个孩子般蹲在街道上,目光越过废墟,仿佛在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居住的洞穴。他似乎想把自己埋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 小路终于打开了房门,她苍白的脸上依稀可以看到泪水的痕迹,她虚弱地说:“他就蹲在路边么?叫他进来吧,给他个房间住。” 我笑了,说:“那你准备一下去接待他吧,他像个孩子,我怕我的样子会吓坏了他。” 小路点点头,在我转身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小木,你帮我梳头吧,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镜子很明亮。我从镜子里可以看到,烛光下一个苍白美丽的姑娘,姑娘的身后有一段满是伤疤的木头,木头粗糙的手里捏着一把精致无比的梳子。这景象在很多年以后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假如那是一幅画,肯定有一个忧伤的主题。 我因为害怕自己粗糙的手会将她的头发弄乱,所以略微踌躇了一下。然后,我蠕动着自己的手指,忍不住去抚摩她的头发。原来,她的头发是如此柔软而富有弹性,这让我想起那些死去的战士,他们会在休憩的时候,无比疼惜地抚摩已经擦过千百遍的枪身…… 在这个时候,让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手起了奇异的变化,木层像伤疤一样脱落,我看到了木层下面如婴儿般洁白的肌肤。 小路微笑着打开门。风吹进来,她的发丝在风中飘动。此时,她看上去像天使一样光彩飞扬。她的眼睛望向少年的方向,声音有如公主一般:“嗨,远方来的孩子,欢迎你来到这个废墟小镇。” 少年惊讶地看着她:“你是谁?童话里的天使吗?” 小路依然微笑着,她说:“不,我是废墟里的公主。” 我为少年打扫出一间房子,就像少年要求的那样——他喜欢房间里有一扇窗,朝着河流。然后我就躲了起来,我要躲开那个少年,因为我是如此妒忌他的口琴,他的忧郁。 因为他是少年,我是木偶。 第二天,少年用他的口琴为小路吹了一首曲子,我听得出来,那是《Titanic》的主题曲,小路开心地说:“原来,你也喜欢这个故事。” 少年说:“不,我仇恨这个故事。为什么人们一定要用悲剧来打动人心呢?” 小路说:“你有爱人么?” 少年埋下头:“我的爱人在城市里吧,可是我走了很多路,没有看见城市,只看到了废墟。” 小路微笑了:“她一定很美丽,并且坚强地等待着你的到来。” 少年捏着口琴,他的手指拂过上面的音孔,说:“如果我找到她,我会每天为她吹口琴,然后为她写满一百首诗。” 小路幽幽地说:“真好,那为什么吹给我听呢?” 少年迟疑了一下说:“为了你美丽动人的眼睛。” 小路依然端坐在椅子上,嘴角的微笑那么轻盈。她的头发整洁,细长的手指摆放在膝上,眼睛望着窗外,看上去依然那么明亮。她说:“你知道么?城市变成了废墟,我的眼睛也看不见了。” 第三天,少年告诉小路,远方的城市也变成了废墟,一路上有很多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家园。他们经过这里,有些人就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个会做拉面的小伙子。他在这里开了一个面店,带来了北方咖喱的香味,吸引着每一个路人。 小路说:“我也有个朋友会做拉面,不知道和那个小伙子比起来谁做得好吃。” 少年微笑着拉起小路的手带她去吃拉面,他说:“你让我住在你的旅馆里,为了报答你,我请你吃拉面吧。” 小路跟在少年身后慢慢地走着,路上很颠簸,小路一不小心脚下踩了个空,少年急忙扶住她,将她更拉近了自己。 小路微笑着说:“你的手比女孩子的还要柔软,但是真温暖。” 风吹过来,远处的硝烟早已消失殆尽,北方咖喱的香味在风中飘着,依稀还有留声机里的歌声,人们的喧闹声。这一切对于小路来说,就像是回到了从前。人们聚集在一起饮茶侃大山,讲着一些传奇的故事。那些传奇里总是有英俊的侠客,他们大口喝酒大碗吃肉;传奇里也总有风尘的女子,小路从不会觉得那些女人的腰肢比自己的细。 香菜的味道,咖喱的味道,牛肉的味道,人群的味道让小路着迷了。她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有这么多人在她身边了,这让她感到很舒服。小路说:“面很好吃啊!我那个朋友做的面虽然也好吃,但是没有这里热闹。” 少年说:“假如你喜欢热闹,我明天再带你来,不过……”少年的声音低沉下去,“后天我就要走了。我要去走一百个地方,写一百首诗,折一百支河边的芦苇。” 小路凄凄地笑着:“那要走多少双鞋子,写多少时光,折多少个春天呢? ” 少年看着小路的眼睛,说:“我不知道那是多少时光,但是我知道只要写满了一百首诗,我就会回来找你。” “你用你纤细的腰肢牵动了春风 春风迷离了远处人的眼睛 你弯下腰去系紧你的鞋带 远处有人用口琴声吹动了你的悠悠长发” 少年在留下这首诗就离开了。他的口琴声转过废墟的拐处,终于消失不见。 我从阴影里走出来,帮小路梳头。我告诉小路,那首诗写在洗得白白的手帕上,手帕上曾经的花纹淡得都快看不见了。我把少年离开的方向也告诉了小路。她冲那个方向扬着手,嘴角的微笑一直保持得很好,好到我都不忍心告诉她少年已经看不见了。 她喃喃着说:“他为什么要走呢?啊,他一定低垂着头,衣服的扣子扣得很整齐,眼睛里满是迷惘和倔强,左手紧紧握着那把口琴。” 我说:“他是个诗人,或许有着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就像他说要写满一百首诗之后回来找你,或者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完美吧。” 小路说:“是完美的悲剧吧,我想我大概活不过这个秋天了。”她笑了,夏天的阳光照进来,在门上的红漆上反射。红色的光芒均匀地洒在小路已见消瘦的脸上。她的脸像是涂了胭脂,也如死亡之前的光芒,圣洁而凄凉。地上,一丝丝掉落的头发随风而动。 我落泪了。木偶落泪了。那泪水丝丝地滑过我的脸,木层一片片脱落。我可以感觉到脸上苍白的人类的肌肤。 外面的草在疯长,疯狂地生长,因为它们知道,它们活不过这个秋天。 树叶都落光了。小路的身体日渐虚弱,头发用手指就可以梳得很整齐了。从少年离开的那天起,她就总是天天坐在门边,那是第一次遇到少年的地方。这个美丽的姑娘有时沉默,有时仿佛很狂热的样子。她说:“你看,枯黄的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被风卷成堆,踩上去就会沙沙地响。小木,你听到沙沙的声音了吗?是他回来了吗?” 但是这个秋天并没有像小路描述的那样美丽,因为新生的树木很少,叶子也很少。我只在一些画里见过小路说的秋天。那些画是从一所老旧的房子里搬出来的。它们被挂在旅馆后面花园的走廊上。一开始小路天天都去欣赏,但是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小路看不见了,走不动了,她还是要告别她所喜欢的秋天了。 秋天已经来了,小路如季节一样忧愁。她或许已经明白不可能等来那小路的拐角,不可能等到少年一步步地走回来。 我对小路说:“秋天还没有来。一个夏天的行者,背着和他一样高大的行囊,手里拿着手杖、毡帽,从远处朝着你远远地来了。” “他必定刚刚吃过咖喱牛肉面,很随便地抹着嘴,然后又很随便地在裤子上擦拭着;他的衣服满是汗渍,破旧不堪;胡子茂密邋遢,皮肤黝黑但很健康;他的眸子快速地转动着,似乎总在寻找着什么;他是有活力的,肌肉匀称,胸挺得很高。 对不对?” “他看见你了,小路。”我像以前一样退了出去。 那人说:“我叫高原,我从世界上最高的草原来。我听一个诗人说,这里有一位公主。他每天都想念你,因此我非常妒忌,我得想办法把你带到草原上去。那里会让你每天幸福得喘不过气,那里还有毒辣的太阳,它会将你晒成黝黑的健康的女皇。” 小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问高原:“你是王子么?王子应该有高贵洁净的衣服,王子应该有他的随从,应该骑着洁白的骏马,走着大路来。” 高原说:“我就是王子,但是我拥有的是望不见边际的草原。太阳从草原这边升起,从那边落下。我还有数不尽的羊群、马匹、牦牛,天上的星斗不过如此。这些,应该比随从、衣服和世俗的排场实在得多了吧。” 小路笑得更开心了。她说:“那么,我的王子,你想要寻找什么?” 高原很高傲地回答她:“我要你嫁给我,我的公主,我要你忘记那个落魄的诗人,跟着我去世界上最高的草原。” 小路想了想,说:“我为什么要嫁给你?我的心随着那忧郁的写诗的少年去了,他答应我在写满一百首诗、折满一百支芦苇的时候回来。” 高原说:“前面的路上满是战火,一百首忧愁的诗不能带给你任何快乐。现在已快到秋天了,哪里还有一百支芦苇?” 他又说:“假如你嫁给我,我尊贵的父亲会送给你五百只可爱的绵羊。你将拥有大片的绿地,种你爱的花。我的草原上每天都是夏天。” 小路忽然沉默了。她的脸红红的,像是幸福的红晕。她幽幽地说:“原来秋天快到了……我是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不可能总是过夏天。我的秋天就快到了。” 高原很久都没答上话,他坐在地上唱起了歌。那种语言小路不曾听过,但是那嘹亮而婉转的曲调告诉小路,这个粗犷的男子的爱情无需躲藏。 小路静静地听着高原把歌唱完。她看着高原的方向,想像着这个高大的男人满脸的胡子,眼睛里充满了野蛮,也充满着似水的柔情。她叹息着说:“把你的胡子刮干净吧,明天这个时候我还想听你歌唱,用你高原上的喉咙,在这个秋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小路第二天并没有去听王子的歌,她病了,病得连坐都坐不起来了,她无法去见那个高原的王子了。 我去看望她。她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整个人都在颤抖。内热使她的嘴唇布满水疱,胸膛起伏不停。她问我:“你知道这样的痛苦么?身上每一处都如针刺般的疼。” 我说:“我不知道。”可是我没有告诉她那些山上的日子,子弹洞穿我的胸膛,蚂蚁啃啮我的躯体,水让我的身体腐烂了,那痛苦也是如此吧。 我只是告诉她:“高原在外面一直等着你。他刮干净了胡子,衣服也变得整洁了,英俊如帝王。” 小路稍稍停了喘息,她找寻着握住我的手,很久才努力地说:“小木,你念首诗给我听吧。” 我于是念了一首诗给她听。木偶不懂得诗歌,我只是将心里的话说出来而已:“远处有个小镇,镇上有个姑娘,姑娘爱秋天,姑娘很漂亮…… ” 小路又说:“那你唱歌给我听吧。” 我于是唱起了歌,木偶的嗓子像个破风箱:“远处有个小镇,镇上有个姑娘,姑娘爱秋天,姑娘很漂亮…… ” 小路突然笑了,她说:“我想见我的王子。” 五分钟后,高原来了。高原和曾经的少年一样,用他的大手握住了小路的小手。 小路问他:“我的王子,高原上的女人是怎么样的?” 高原回答说:“她们一生都在舞蹈。她们大胆而美丽,若看上了某个男人,会扭着腰肢坐在他身边,用细软的手指轻轻地拂过他的脸。” 小路圆睁着眼睛,伸出手去寻找高原的脸,很神往、很甜蜜地说:“那你带我走吧,我喜欢高原,我要自己幸福得不能呼吸,躺在你的怀里。” 这个名叫高原的青年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他的呜咽在小镇的每一个角落回旋。 但是废墟还是废墟,秋天还是秋天,除了呜咽,小镇孤独无语。高原走了,他说他去找最快的马匹,明天带着小路去没有秋天的地方。 那个晚上,只有我静静地陪在小路身旁,握着她的手。她的热度渐渐消退,她的身体渐渐冰凉。只是她一直都没有发现我的手是热的,这些日子里我有了一双温暖而且柔软的手。 她说:“木偶应该没有泪水,因为木偶不懂得感情。小木,你说对不对?” 我说:“少年从远方带来了消息,他已写满一百首诗,正星夜兼程地往这里来。” 我说:“王子丢弃了行装,他每天都会把脸上的胡子刮得非常干净。他已经放弃了他的王国,将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 我说:“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后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个少年,多少个行者将看见你的美丽。” 小路高兴地笑着,那些气流让她喘息不止。我握住了她的手,继续说:“那你怎么办啊?世界上只有一个小路啊,小路,你知道么?” 小路微笑着,轻快地哼起了那首《Titanic》,一遍又一遍。她说:“小路知道,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小木。他是个木偶。小路要这个木偶去告诉那个写诗的少年,小路等着他为我写一百首诗,一首首读给我听;小路还要这个木偶告诉高原,我以后天天都要去听他唱歌。他的绵羊有多少只,也要为我唱多少首。” 她又咯咯地笑起来。终于,她满脸甜蜜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心脏在某一个最柔软最顺畅最温暖最怀念的点,停止了。她握着我的手就此松开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小路,她死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木偶,他还活着。 这个小镇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不会再有人来了。方圆几百里都被铁丝网围着。这种标记让所有的人对这块土地望而却步。这是不祥之地。 小镇其实并没有什么北方的少年,带来咖喱的香味,让小镇热气腾腾起来。 小镇没有来过写诗的少年,带着口琴,去写一百首诗,去折一百支芦苇。 小镇没有高原来的王子,满脸胡茬,千里迢迢来寻找他的公主。 小镇也没有聚集的人群,每天吃着拉面,无聊时谈论着天花乱坠的故事。 其实,小镇上只来过我一个人罢了,而且我只是个木偶。 我曾经阅读书籍,看电影,学着往面条里加入咖喱,学着写诗,学着唱歌,学着各种各样的本领。 我也曾把电影中嘈杂的声音录下来,用留声机大声地播放出来,因为这会让人听起来产生一种这里很热闹的错觉。 我是个木偶。在小路的手松开的一瞬间,我的身体冻结,依然是块木头。 我说上帝,我不是人,我入不了天堂。 我说佛祖,我若得了道,我就是个树妖。 我该走了,回到我的山林里去。我的敌人你来吧,我的手指已经抵住了扳机,只要你进入我的十字镜,只要我的手指关节还没有锈掉,只要我的脑子还没有腐烂掉,我就要向你开枪。也许这样我便可以忘记那些人,那些事情。 我也偶尔会回头看一眼。在我的身后,一个小镇建立起来,它又在刹那间毁灭了,然后我站起来,夕阳是如此美丽,射穿我满是伤痕的身体。 (《青年文学·下半月版》2005年2月)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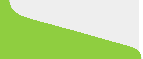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