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吧,记忆 |
|---|
| http://y.sina.com.cn 2005年07月19日 15:47 《成长》 |
|
作者:一痞了之 我出生在马贡多,叫奥雷良诺,莫非这是一个受诅咒的名姓?人们说我在娘肚子里就会哭,生下来时就睁着眼睛。是的,有谁知道我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呢?我飞快地指认出陌生的一切,我牢牢盯视着棕榈叶遮盖的顶棚——在风雨中它显得摇摇欲坠。我似乎一出生就在等待一场毁,一场要耗尽我的一生,容纳我所有孤独的毁。当雷声让所有人掩起耳朵,我才悲哀地呼喊起来,“我会经历无数冒险,我会有无数女人与儿女,但命运啊,你为何时刻提醒我——我等待的只是一场毁,一场《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 关东大地震后的第四年,我两岁。我时常对大人说,我记得那时的光景,不料他们总是笑我,竟用一种淡淡的憎恶的眼神望向我,我的脸一直很苍白。可是,我能有板有眼向你描述我当时仍用着的洗澡盆——一个崭新而光亮的树皮盆,水舌轻舔着盆沿,光柔和地映照在水面上,小小的水波相互撞击。也许从我两岁开始我便爱上了一切绚烂至极的东西,像樱花、红润的脸、强健的肌肉、甚至英雄的死亡。也从那时人们开始不相信我,我最裸露的心声亦被称作《假面自白》(作者:三岛由纪夫)。 在我3岁的时候曾有个愿望——做一名铁皮鼓手。我严肃而坚定,相信自己不需要追随者便能夺得权力的意志。是我错了吗?岁月在我身上留下了病态而神奇的烙痕,我是3岁的孩子,神话里的侏儒。3岁的我失落于再无法重返母亲的子宫,3岁的我唱破一地碎玻璃,3岁的我敲出任何人也跟不上的鼓点,3岁的我擂起鼓槌,把一场游行变作狐步舞会。它就在那里——我的驼背之前,肚皮之上,崭新的,红白两色锯齿相间的——《铁皮鼓》(作者:君特·格拉斯)。 也许命运要彻底击溃一个人,并不用那疾风骤雨般的突袭,而是一寸寸的逼近,将生活的火焰一丝一丝扑灭。在回忆4岁的光景时,我总是心怀惊惧的走进《都柏林人》中的《对手》(作者:乔伊斯),在那里我只是个小配角。父亲是公司小职员,他每晚都喝的酩酊才回家。我在黑暗里静静等候他那而浸满酒气的跫音,4个哥哥睡的很熟,我得赶快爬起来为父亲开灯。我不敢瞧他的脸,他会打我,我不敢丝毫怠慢,他会打我。哦父亲,求你住手好吗,我会为你唱“万福玛利亚”;哦父亲,不要因你承负命运的罪责而发泄于我好吗,你瞧我羸弱的肩膀,我那时可只有4岁。 5岁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死了。他是老福林神父,那是他第三次中风。每个傍晚我玩耍回家,都见他的房里亮着微弱而平稳的灯光,一如他那微弱的呼吸。收到他死亡的消息时,我未显震惊,我还远不懂得什么叫作死亡。几天里我仍时常推开那扇厚重的门,阳光穿破尘埃,我期望看到老神父就坐在角落的椅子里,摊开手掌录出糖果。可是没有。他不在了,迎接我的总是他的《姐妹们》(作者:乔伊斯)。他远行了吗,还是躲进黑暗里?我揣测着他的去向。死亡,这厚重沉郁的词汇,对我5岁的耳朵,只是一阵过堂风。 我在一幅照片面前停驻良久,照片中的男孩是我吗?那孩子应该只有6岁。车站广场上空无一人,很久以前,我在这儿玩耍过?我真的记不起了,我失忆了。我摸索一条条线索,寻访我的后方,欲求找回记忆。可是当面对这张相片,我却别无所求,只求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他的笑容明亮而纯净。是我吗?我那时一定很贪玩,踢球要一直到傍晚。我带着球跑,穿过林荫道,夕阳的余晖洒落我身后。我只是跑着,跑过《暗店街》(作者:莫迪亚诺),跑过一扇扇橱窗,毫无忧伤的跑着…… “明天可会是好天气?”在我7岁的一天下午,我不停向父母吵嚷着要《到灯塔去》(作者:弗吉妮娅·伍尔芙),我心中所念维系灯塔。我想有的时候,人真会一夜长大,那天突如其来的大雨击碎了我到灯塔去的愿望,却又让我窥着一线天光,仿佛体悟到了世界的本真面貌——一个陌生的寄居之所,而我们都只是匆匆过客。依稀记得彼时,母亲也说了类似的话……“詹姆斯,灯塔到了。”船在水面飘荡,父亲转过身与我说了这句话,此时已距7岁的那天下午有10年了。10年,多少人走远,多少人走近。就象盘旋头顶的海鸥,有些好奇的飞来,有些鸣叫着飞远。我始终记得那个所有人都无能为力的下午。 8岁的夏天我是在海边度过的。风很大,像往常一样我一大早就赶去老人的茅棚,呵,他竟然回来了!瞧他那双伤痕累累的手,他坐在床上呼呼喘着粗气。身旁没有鱼,他被打败了。后来的几天我一直待在老人身边,替他煨些咖啡,给他安慰,几天里他又苍老许多。有天夜里我,我从老人的茅棚退出来,临走时为他掖好被角,只听得老人梦呓,“我没有被打败,我没有被打倒……什么也不是,是我出海太远了……“我的眼泪也簌簌落了下来……离开海边很久了,我的心却时常回到那儿。老人给我勇气,他就像头永不服输的狮子。哦,我很乐意向你讲述他的故事,《老人与海》(作者:海明威)。 越过庄园,就是俄罗斯典型的阔大的田野。在无数花朵的熠熠微光之上是蝴蝶翅膀的光闪。我9岁的时候开始漫游。经常骑单车,到6公里以外的田野和森林中玩耍。在7月的日子里,我躺在长长的河岸上,仰望天空,嘴里咀嚼着植物的茎秆。河对岸那片开阔的沼地让我有种冲动,想要一睹为快,似乎那儿也寄托了少年的我对彼岸之美好的期冀与幻想。呵,记忆,你还羞涩什么?《说吧,记忆》(作者:纳博柯夫),说吧,记忆。少年的时光已随蝴蝶飞远,你还不趁机把它召唤! 那年我10岁,人们叫我尤拉,多年以后他们唤我《日瓦格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当我像狼崽一样仰天嗥叫时,人们惊呆了。天空洒下疾雨,舅父过来要领我离开。我不冷,我想守在这儿,温暖我墓穴里的妈妈。我不明白老天为何那般残忍,就夺走了她;可老天有时又好软弱,我一哭鼻子他就下大片大片的雪花......我独自一人时,忍不住会呼唤母亲。有天我走近一条沟谷,沿着土坡下去,是长满谷底的赤杨树丛。地面上到处是果实,吹过一阵风,我似乎听到她正在回答我的呼喊,“啊,我的妈妈!“我心中充满悲伤,双膝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就在昏厥之前,我诅咒了命运,我再不许你轻易从我这里夺取心爱的一切! 我最后一次坐在家人中间吃饭是在11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从那以后我爬上了树,誓死不再下到地面。就在这一年,我第一次恋爱了,恋上的是秋千上的金发公主薇莪拉。我轻念她的名,发最后一个音的时候舌尖抵住上颚,凝滞地弹一下,仿佛预示着她的形象要在我心中卡住一生。多么讽刺的事情,我一边决绝地抵抗着这庸常的世界,一面又贪恋着象征世俗美好的薇莪拉。我在翁布罗萨高大的栎树间飞来飞去,谁能告诉我该如何解开那些困厄,啊,我毕竟只有11岁,却要永远背负这座称号——《树上的男爵》(作者:卡尔维诺)。 你相信吗,我第一次替人保守秘密是在我12岁的时候,而那个人是我母亲。温柔夏夜,一位男爵向我走来,我满心欢喜,很自豪能拥有一位大朋友。旅馆里的灯光太过明亮,我邀请我的男爵朋友到户外扑捉萤虫,瞧他那闪烁的双眼,我就知道他也爱这一切。可是我错了,后来我终于晓得,他其实感兴趣的是我母亲,而不是我。男爵并不渴望与我做朋友。那天晚上,就在男爵与我母亲相拥的瞬间我突然跃出来,吓他们一跳。呵,母亲再也不会爱我了,她会只顾着男爵。我的头脑里紊乱极了。后来的事情我不想再说,因为我心里有些事情已经破碎了,再也合不好,就在那《灼人的秘密》(作者:茨威格)成为秘密之前。 母亲一直渴望我成为一个非凡的人。她在我13岁的时候跟我说,“雅罗米尔,你该继承阿波罗的七弦琴呢。“她常常用恳求的目光望着阿波罗雕像,她是更爱我,还是更爱阿波罗呢?那时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求,每天到一位画家处习画,受些赞誉或责备,全然不会在乎。谁会想到呵,多年后我会成为一个蹩脚的诗人,在贫瘠的精神世界里失落我一个一个的梦。《生活在别处》(作者:米兰·昆德拉),也永远只在别处。我当初为何要写下那些微弱的诗句,在我的13岁?我当初为何要怀些无名的忧伤,在我的13岁?我在水的柔波里诞生,却在激情的泥淖里耗掉一生。 我14岁的时候死过一次。我父亲早亡,母亲是精神失常的钢琴师。13岁那年,我随作家爱德华回到巴黎我祖父拉贝鲁斯身边。爱德华正写一本书,名叫《伪币制造者》(作者:纪德)。我最后的那天和往日没什么不同,只是我口袋里多了一柄手枪——我输掉了游戏,代价是用枪口抵住太阳穴,扣动扳机。参与游戏的人都说枪里是没有子弹的,但是你知道,那里面是有的啊!……在我魂魄散尽之前,还听到爷爷慌乱的叫喊,“魔鬼与上帝原是一样东西,他们狼狈为奸……“上帝牺牲了他的儿子,爷爷失去了我——他的小波利。 在我15岁那年,小妹一直担心大哥皮埃尔会杀掉我。而我知道,妈妈一直担心的是皮埃尔,不是我。小妹和我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紧紧相拥,她温我的头发、脸、放在胸口上的双手。她会很轻声的呼喊我,“保罗,我的宝贝,我的孩子。“夜鸟在啼,我们拥抱再紧亦觉寒冷。那一年,我和小妹喜欢观望同一片天空,先是一起看,然后各看各的。再后来,小妹有了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向我描述她们第一次做爱的感受,她的恐惧,他的温存,无可比拟的大海的啸声,以及夹杂在那首“绝望的华尔兹”中的肉体欢悦后的失落感。 天啊,我的16岁根本不值得一提。我曾经的理想是作个《麦天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呵,“麦天里的守望者“,多好听多纯洁的一个词,可我现在压根就不再相信——它不过还披件美丽的外衣,而在我心中它早已发了霉。那天傍晚,我忍着滴鼻药水的浓烈味道走进老斯宾塞的房间,作最后的道别。70多岁的老头一个劲儿跟我提什么人生是场球赛,“霍尔顿,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我鸡啄米似的点头,心中却在默数着老人头顶寥寥的几根黑发,真不简单,他竟然还有黑发!可是人生会是球赛?别开玩笑了,就象老斯宾塞的白发那样压倒性的占据球场,球还怎么踢?16岁的病的不轻,谁能在我奔到悬崖之前把我捉住。 我在17岁的时候作了一个旁观者。躲在草丛后面的黑猫嘴边淌着涎水,注视着熟睡中的马尔克的巨大喉结。喉结大的出奇,一蹿一蹿好象老鼠,那只黑猫就扑了上去……那一年我见证了许多事情,战火的蔓延、人们对英雄的崇拜、马尔克偷走十字勋章,并永沉海底。在深海里,他的喉结可是安静下来了?如今,我以回望的姿态看我的17岁,看那狂热的年代。似乎每个人都被一股巨大的力推动向前,眼里散放光芒,追逐德意志的统一价值。殊不知,他们才是被追逐者——被时代放逐,被时代驱赶,两厢纯粹的如同《猫与鼠》(作者:君特·格拉斯)! 18岁,在我心中这一直是个响亮美好的词。我在少年时代无数个清澈的夜幻想我的18岁,我亦要在未来的岁月里一再召唤我的18岁。每当我走近《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作者:乔伊斯),我还能听到母亲在我18岁时所说的话,“斯蒂芬,我如今祈愿的就是你能独自生活,远离家园和朋友,了解这世界,了解你的心。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理想的蓝莲花是否已绽放,青春的翅膀是否已迎风?生活啊,让我们开始吧。 19岁,我又恋爱了。我喜欢上一位《伊豆舞女》(作者:川端康成)。舞女看上去约莫17岁,梳着大发髻,鹅蛋型的脸乓匀称、极美。她的貌美与明亮的秋色,让我的心一颤一颤……舞女在我面前总显羞涩,很容易就臊红了脸。她端茶过来,茶却洒了一地,舞女拘谨的用手巾揩着铺席。此刻回想起来,她那快活的笑声尤温润耳畔。我领她到许多地方玩耍,我们彻底忘却世俗身份的拘囿。可爱的丫头,我几乎就要告诉你,我恋爱了。后来我因故告别,我还有学业,在船上我远远瞧见她不停挥舞的白手帕。呵,伊豆的舞女,不论现实的大船载我去何方,我都要再将你寻回。 终于回到这里。走过2004年我的20岁,走过一场暖冬,而我仍贪恋蜷在被子里阅读或书写。作一个读者是美好的事,似曲颈弯向黑水的天鹅缓缓游向拱桥下的阴影,我的心也顺从的滑向每个故事的深处。在那里,我单纯的忧伤或快乐;在那里,我拾取片片光闪的碎片或影象。我可以咧开嘴笑,为着什么原因,或者什么也不为,手中的书让我感到生命的丰盈与厚实。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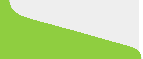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