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届校友郭小聪:温文尔雅的力量 |
|---|
| http://y.sina.com.cn 2005年08月04日 14:47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
|
作者:74届郭小聪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 不管世事怎样变迁,一所好中学的素质应该是内在的和基本稳定的。在正常的年代,人们认定的好中学自然倾向于看它是否与好大学的校门绵绵相通。而在动乱的年代,好学校的根基就象海岸边的礁石裸露出来,既不会因为排名名次的波动而增减,也不会因为升学率等硬指标的消失而消失。至少从我当年上高中的体会来说是这样。 我是北大附中“文革”中的第一届高中生,我是千百名就近入学来的71届初中生的一个。在此之前,北京市的高中已经停办五年了,“复课闹革命”使正常的教育秩序几乎荡然无存。直到70年代初,形势才似乎有所好转,大学首先恢复招生,我们到北大欢迎过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校,也听过北大哲学系一位46岁的新学员来附中做讲用报告。那真是一个得听从命运的时代。我记得北大附中宣布上高中同学名单的那一天是1971年12月10日,一个干冷的下午,在学校大饭厅里,大约90名同学入选,十个初中班鸦雀无声。挑选过程是不公开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那时我们的年龄已经大到开始学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了,但还没有大到足以理解这也就是命运。 上高中才第一次有了上学读书的感觉。我们第一次到尘封了好几年的实验室里上化学课;第一次从学校图书阅览室里借书;第一次有很多作业要做;第一次感到期末考试和分数的压力……。这些对今天的中学生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内容,对我们那时却象是享受。是的,当大多数同龄人被过早地中断学业抛向社会时,我们又怎能不是在享受学习呢? 学校对我们这一届高中非常重视。各任课老师对我们倾注了可以说是充满激情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期末英语考试。戴述姜老师不辞劳苦地花两天时间搞了一次令大家紧张万分的听力测验。她叫同学们单个进来自由选题,老师把所选的英语故事连续念三遍,就要同学马上翻出来。这种对我们有点象赶鸭子上架的高水平要求和测验方法,在连外语学校都停办的“文革”中是难以想象的,后来跟谁说都感到惊讶。老师们还额外为我们两个班办了各种课外讲座,自由参加。我记得班主任杨贺松老师给我们讲了《水浒》语言研究,从内容到讲法都与中学明显不同。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这就是大学式的专题讲座,老师概括的是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而我们享受了大学生的待遇。在中学质量普遍下降到小学水平的年代里,我们在北大附中却能听到大学水平的课程,这在“文革”的浩劫里又怎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呢? 说起来,北大附中有相当一部分师资原来就是来自北大的教员,是“文革”前北大陆平校长根据“四级火箭”的长远设想而从各系选调来的教学骨干。我至今记得教数学的颜同照老师从我位子旁走过向大家提问时那哧哧带笑、沙哑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曾是北大教学系的高材生。上他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举重若轻,我想除了他开朗幽默的性格外,还因为他过人的才华带来的自信。这批老师毫无疑问是北大附中最大、最独特、可能也是让市里其它中学最羡慕的一笔财富。而且作为精神财富,这些老师并不因陆续退下讲台就遗憾地失去价值,我想正是通过他们当年把北大的已经形成传统的比较自由开放的学习风气传播过来,才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北大附中今天的校风;今天北大附中的学生们才可能即使在题海滔天、竞争激烈的应试教育环境里,也还能相对保持知识广泛而真实的兴趣、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性潜能和比较开放的心胸。这样的校风可不是用分数线、升学率等硬指标所能衡量和造就出来的。 现在想来,学校和老师们当初不是非得把高中办得这么认真的,当时没有任何规章制度和可见的希望催促他们去做。学生学得再好两年后也要去上山下乡,老师教得再认真也不多拿一分钱,相反倒有可能在某次政治运动中招来“白专”的指责。但这就是好学校、好老师的素质。“文革”时代最荒唐之处就是它是一个不许人们敬业的时代,这与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和天性根本背道而驰,他们渴望学校象个学校、老师象个老师,能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施展报负和才华,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尊严。越是好学校、好老师,这种愿望就越强烈;只要有一点机会,就会迸发出来。所以,尽管没有任何其它激励措施,只是接到上级的一纸恢复高中的命令,学校就依然有声有色地干起来,老师们就义无反顾地迅速把教学恢复到高水平,久被压抑的职业自尊就很快反弹为神圣的工作热情。这就是一所好学校对连敬业都需要勇气的荒谬年代所做出的最自然的回应和蔑视,这就是北大附中在普遍低潮的年代中所显示出的真正实力和活力。这是显然无法被量化的,但是更真实、更可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命运对我们个人发生了作用,我们成为直接的受惠者。尽管上高中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出路,尽管我们以后也同样历经曲析,但是在关键的年龄期里,我们受到了知识的哺育,而且是充溢了爱与美的情感教育和洗礼。我记得高一班主任杨贺松老师象慈母一样关心着班里的每一位同学。我记得高二班主任江蓝生老师借给我《普希金抒情诗集》时再三叮嘱我不要跟别人说,但她还是冒着风险借给了我,我也由此第一次感受到世界一流抒情诗歌境界的美丽、美好和庄严。当时我已经十八岁了,书店里除了样板戏式的读物外,简直是什么好书都找不到。但是,任何野蛮倒退的力量最终都敌不过知识的温文尔雅的力量。当时我可能还不能清楚地概括出这个道理,但是生命已经浸润其中。凡事总有报偿。我们在学校老师的真诚受护下正常成长,也就培养起一个正常人的做人准则、情感和良知。“文革”中叫我们批判“师道尊严”,我想都不用想就觉得是谬论,在我们身上倾注心血的老师怎能不是好人?事实上我们和老师的关系非常融洽并充满敬意,我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永远永远尊敬自己的老师们”。“文革”中盛行“读书无用论”,但事实上正是在高尚的教育环境里,我们才越来越感到自己对这个社会负有责任,对自己也抱有信心。十七八岁正是刚刚成人的时期,给一点爱护和鼓励就可能一生走正道,别人认为我们是有用之才,我们就可能是有用之才。当然这不是仅仅指做出多大贡献,而是指成为一个对自己的生活认真负责、对社会有益而无害的人,这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如此。 成长在“文革”中不能说是幸运的。但作为北大附中“文革”中的第一届高中生,我始终觉得那两年生活就象是处在台风眼的中心。尽管周围的政治运动还在继续,有时风浪就泼溅到老师身上,但我们尚能在学校老师们尽力供卫的一片宁静的小天地里安心学习,乐观成长,这在那个时代真不容易。尽管时间有限,尽管事实上第二年台风眼已有所转移,学习受到干扰,开始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但这对我们一生的潜在影响已经注定。越稀缺的越可贵,在动乱的年月里,那圣殿般的课堂、诗篇般的课本,一天上课后略带疲倦的满足和放学路上懒洋洋的阳光……,不管以后我又读了多少年的书,我都忘不了这段诗意般的启蒙时光。我想这段被见证的历史,不仅是我们个人命运中的一个契机,也是北大附中校史上显示出非凡凝聚力的转折的一页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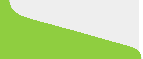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