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酋长“失踪”了 |
|---|
| http://y.sina.com.cn 2005年01月10日 18:37 新浪校园 |
|
1.酋长“失踪”了 湄沁打来电话,说酋长失踪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和沫沫在床上那个。床顶,天花板上的灯光冷不丁地一闪,一闪。我记得在开始之前,我是关掉了这盏灯的。可不知为什么,它总在关键时刻,眨起了贼溜溜的眼睛,像有人偷拍一样。沫沫搂着我的腰,紧张得要命。她说,我怕怕。 这是一盏国产环形吸顶灯,沿海某个城市引进的日本技术。酋长建议我买它时,说它寿命长,光线强,用电省。为此,我花掉了一百多块。酋长是路灯局的电器工程师,简称“电工”。他的话,我信。 买回后,最先发现吸顶灯还有“偷拍”功能的,是沫沫。那天半夜,我们在床上,也是不早不晚的当口,它忽悠地一闪,又一闪,把沫沫吓哭了。后来,我问酋长,在断电的情况下,日光灯管为什么会突然发光?而且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在我和沫沫接通之前?酋长解释说,在物理学上,那叫“放电现象”,正常得很。就像一个精血旺盛的愤青,你阻止他性交,他就会焦灼不安,然后擦枪走火。可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日光灯管在断电之后,仍然放电;也不是所有的愤青,在按捺不住之后,都会擦枪走火。 湄沁一直在哭。 我丢下电话,提起裤子,对沫沫说:“我得出去一会儿。” 沫沫问:“你去哪?” 我说:“我找酋长!” 沫沫不依不饶,她躺在床上呻吟:“就五分钟。” 我是片刻也不能等了,我得找到酋长,问他今晚是不是擦枪走火?我刚刚迈出房门,沫沫就在背后破口大骂:“毛次!你最好去死!” 毛次是我的名字。 湄沁还在哭。她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我劝湄沁冷静。问他们有没有吵过架,酋长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仇人?湄沁直摇头,说没有,真的没有。酋长那么老实,怎么会呢?我仔细一想,也是。 六神无主的湄沁,不忘给我递上一杯开水。我说,还是你喝吧,喝完了慢慢说,酋长是什么时间、在什么情况下失踪的。 情况是这样的:湄沁做好了晚饭,等酋长下班。可酋长到了该回的时间还没回,他以前一直是很守时的。奇怪的是,现在已是凌晨一点多了,人不回,手机也关了。他会不会出事啊? 湄沁像有神经质,她从座位上弹起来,要冲出去找酋长。我拦住了她,问有没有打路灯局的电话?湄沁说,打过了,一直在打,没人接。我反问,为什么不设想一下,他有可能在哪条巷道,正在抢修哪盏坏掉了的路灯呢?湄沁说,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在这个城市,什么时候有谁抢修过什么路灯呢?我说,那再等等吧。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提议,是不是先检查一下房间,看看酋长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湄沁同意了。 他们的住所在泰格公寓的1栋3楼。不大不小的两室一厅,很快被我们抄了个底朝天。我发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在他们卧室的天花板上,装有一盏和我租住房一模一样的吸顶灯。另一样是,在沙发的隐秘部位,有一本上了锁的日记本,封面上写着“非本日记主人,请勿随意翻动”。 我把日记本交给湄沁。她说,这是酋长的笔迹。我询问湄沁,要不要一起打开?湄沁说,不行!酋长不在的时候,我们不能偷看他的隐私。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酋长的下落的呢?湄沁对我说,在W市,他没有别的朋友,就你这个老乡。如果天亮之前,酋长还不回家,你就打开看看吧,发现了什么线索,就告诉我。 从泰格公寓出来,差不多凌晨三点了,顺着雄楚大街向西步行三公里,我回到了石牌岭的租住屋,沫沫也不见了。 她偷走了我的两千元现金。沫沫总是隔三岔五地从我口袋里偷钱,但平时最多不超过二十元。她玩福利彩票,每期十注,每注两元。可我从没见她中过一次奖,包括最常见的五元末等奖。即使这样,我还是要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任凭沫沫的一只手频繁地探访我的口袋,另一只手不断地指向摇奖机中的“双色球”。沫沫为残疾人作贡献,我为沫沫作贡献。我估计,她拿到这两千元钱之后,现在已守候在街边的某个投注点,只等天亮,彩售人员一打开机器,她就会一口气买下一千注。如果运气好的话,沫沫会立马回来找我,如果运气不佳,她极有可能从此消失。 不管沫沫回不回来,我已经没有心情出去找她了。沫沫和我在一起,总共逃跑过五次,前几次,她带走了自己的行李,这一次,她连行李也不要了,似乎那个五百万的头等奖,非她莫属。 我是半年前认识沫沫的。那时,我刚刚从部队退伍。我父亲打来电话,催我回长沙,说在卫生防疫站给我找了一份工作,但我不想回长沙,我想用五千元退役金作本,开一家小型的户外运动营。当我在W市的街头巷尾,忙于寻找门点兼做临时住处的时候,我新买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这是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发给我的短信,她说,由于误操作,她把刚买的一张一百元充值卡,充到我的手机上去了。她问我,可不可以退还她的一百元钱?我仔细查看了短信上她留下的手机号,竟与我的手机号尾数只差一字,我的手机号是13098830064。相邻的两个数字,极有可能造成操作失误。我还查对了我手机的话费余额,果然多出了一百元。于是,我把电话打过去,答应退钱,我们约好在理工一桥上见面。 原本打算退了钱,就去附近看看,有没有需要出租转让的门点。因为那里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工大路,是“夜香港”。但沫沫执意要拉我去麦当劳,她花了大约五十块,相当于手机充值卡面值的一半,要了两份汉堡,两杯可乐,两只菠萝派,一袋薯条。薯条是我们共吃的,沫沫一边蘸着番茄酱,一边兴奋地说,同在一个城市,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但我们都住在中国联通的隔壁。 吃完麦当劳后,沫沫和我手挽手,一起逛了工大路,我没有发现有需要转让的门点,但在不远处的石牌岭,我意外地找到了一间出租房,也就是我现在的租住房。我的房东,是一位孤独的老太太,我第一次见到她,并向她打听附近有没有出租房时,她坐在一幢破旧的两层小楼前抽烟,不是普通的纸烟,而是咖啡色的、又粗又长的雪茄。她说,孩子,是你住吗?我说,是的,是我一个人住。她站起来,指了指身后的小楼,说,请跟我来。很窄很黑的前厅过道,吱吱作响的木质楼梯,两只脚一踏上去,心里就直发毛。看来,这幢两层小楼很有一些年头了。我有点担心,说不准哪天它会坍塌下来,埋葬了我。 老太太说,原来没打算出租的,现在身体不行,想找一个年轻人能天天进进出出,好给这老房子添添生气。我问老太太贵姓?她说姓沙。我们就叫她“沙奶奶”。沙奶奶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又嗜烟如命,而且只抽劣质的雪茄。这样,她的气管总像一支风管,有一种杀鸡的呜咽声。又因为听力不好,她说话的嗓门特别大,尖锐的声音也就显得特别刺耳。沙奶奶矮胖而行动不便,有一头亚麻色夹杂花白的自然鬈发,双眼凹陷,但眼神慈祥,温和。我怀疑,沙奶奶有俄罗斯血统。后来,我还听说,沙奶奶一生未婚未育,房下只有一个侄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教俄语。 见到沫沫的第二天,沫沫就把行李搬了过来。她说,我不走了。我说,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 沙奶奶没有另收我的房租。 我从不在乎一个人的到来,也从不在乎一个人的离开,我对酋长的日记有着浓厚的兴趣。可是,我拿着日记,竟不知如何下手。不是我多么胆小,也不是我多么纯洁,而是天怎么老不亮。在天亮之前,我想回顾一下我和酋长的关系,我曾经是酋长大学军训期间的教官。 1998年8月上旬,我所在的武警部队参加了长江大堤抗洪抢险。那个“许大头”许指导员强调,在码放沙袋时,要像平时整理内务一样,保证每个沙袋方方正正。他还要求我们从数百万只杂色编织袋中,挑选出艳丽的红色,在绵延十余公里的子堤上,镶嵌出壮观无比的巨幅标语。那标语叫做“水涨堤高,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在人人表态的全体军人大会上,我第一个跳出来指责“许大头”,说他是“抗洪白痴”,“许大头”则呵斥我是“政治白痴”。这事儿后来被王支队长知道了,他没有批评我,也没有批评“许大头”。于是,子堤继续在“争分夺秒”中长高。8月13日,抗洪部队爆出一条特大新闻,“许大头”的“政治堤”在央视新闻频道中亮相。一位从北京来的记者站在子堤上,手拿话筒,背对长江,采访了“许大头”。立功后的“许大头”,还没来得及卸下胸前的大红花,就急于找我谈话,他让我明天回中队去,参加支队组织的大学新生军训。其实,我早就明白,训练完新生,正好是老兵退伍的时间。 和我关系最好的郝强对我说,妈妈的,凭什么啊?你毛次能名正言顺地临阵脱逃,我们就该在这里严防死守,誓与大堤共存亡? 那时,部队刚刚吹过休息号,郝强从堤坝下面往上爬,他满脸泥污,只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他见我着装整洁,拎着背包,幸灾乐祸地等待返回后方的汽车,很是不服气。 我说,你操蛋吗?你不操蛋就老老实实地扛沙包! 抗洪,给我带来耻辱,也给我带来骄傲。我最大的骄傲,是让王支队长记住了我的名字。不过,他把“毛次”叫成了“刺毛”。管他呢,刺毛就刺毛吧。几天以后,我极不情愿地去警民共建单位——H理工大学,充当了一名教官。虽说这里没有前线那么紧张辛苦,但那段时间,我总想发火。我一看到那些胖胖墩墩的大学生,就把他们当成了抗洪前线的沙袋,就想上前去拧背扛摔。 我选定酋长作为我的发泄对象。酋长戴着深度眼镜,脸庞黝黑,整个一山里人。可恨的是,这个山里人总是在队列中作沉思状,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山里人又像一名社会活动家,身边聚集了不少女生,听他神吹神侃那套狗屁不通的“治国理论”。湄沁就是他的崇拜者当中的一个,她尊称他为“酋长”,说等到大学毕业后,邀约一批志同道合者去非洲丛林,组建一个“中国部落”。 我决定治理酋长。我在操场的草丛中逮到了一只土蛤蟆,我命令酋长给我吞下去!酋长说,毛教官,你这是胁迫部属,而且还是侮辱人格。我当着全体新生的面,大声说,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茹毛饮血”吧?你们明天的部落,就是今天的团队,部落也好,团队也好,头儿永远只有一个。现在,我,毛次,就是你们的头儿! 说完,我把那只土蛤蟆的前肢,连同头的部分咬掉了,并咽了下去。我喊酋长出列,把血淋淋的后半部分,恶狠狠地塞进了他的嘴里。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只要酋长敢把它吐出来,我肯定会扳掉他的两颗门牙。如果他还敢反抗,我就像摔沙袋一样,把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一节课不得翻身。但酋长出乎意料地咬住了土蛤蟆的尸体,他睁圆眼,张大口,把它吞进了肚里。他还把身体向前一挺,大声说,报告毛教官,我可以入列了吗? 我听见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我说,酋长,你有种! 打这以后,酋长成了我的好朋友。后来,我还知道,他也是湖南人,家在湘西。酋长不仅和我同乡,而且还和我同岁。他的梦想是上北京的人民大学,但他的命不好,复读两年,最后报考了H理工。酋长寄读的学校,正是我的母校长沙一中。他说出长沙一中高二(3)班时,我大吃了一惊,我为我没有早些年认识酋长,感到后悔莫及。那时,我在高二(5)班,是“滓子集中营”——普通班。酋长倒先不好意思起来,他说,一个年级那么多人,我们又不同班,你怎么会认识一个从乡下来的寄读生呢?况且,我后来转学去了别的学校,复读了两年,考砸了两次,一直自卑得很!即使是在有名的一中,我也是不出名的,你肯定不会认识我了! 酋长这是第一次在我面前谦虚。我仔细回忆了高中时期那些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同学,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就差抠着脚丫子数数了,竟发现没有一个同学能够和眼前的酋长对得上号。3班和5班就相隔一个4班,那是什么班?是牛叉哄哄的火箭班。我们普通班一帮马里马哈的兄弟,总是正眼都不瞧火箭班那些牛叉的,牛叉们也从来都是埋头读书,没空打量我们这些普通班的马里马哈的。没办法,天生的牛头不对马嘴,搞不到一块去。 但现在,我们相识在H理工大学,他是大一新生,我是教官。 酋长说,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现在的专业。我说,你将就吧,总比我强。我没有读过大学,连高中都没有读完。这一切,都是叫钟小玲给闹的。酋长问,钟小玲是谁?我说,是我的邻居。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同属军转,早年在部队时是上下级关系,后来到地方工厂上班了,还是上下级关系。高二暑期,钟小玲说喜欢我,约我上宿舍楼顶。她很熟练地要和我那个,我当然愿意和她那个,因为她是我们大院的“名花”,也是我们5班的“班花”。那年暑假快要结束时,我趁这不可多得的机会,想和钟小玲再次那个,可她拒绝了我,她说她明天一清早要去西安。我后来见到钟小玲是第二年的春季,她挺着一只大肚子,被她妈领着上门找我妈。我爸听说后,吓了个半死,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儿子奸淫了他上级的女儿。 酋长对男女之事,表现出来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迫不及待地问我,那后来呢?我接着说,后来,钟小玲拿了我家一笔钱,生下孩子,真的去了西安。我十七岁做父亲,这成为我人生的污点。我爸托熟人、找关系,非要把我弄到部队去,接受革命熔炉的教育改造。入伍之前,我爸想把那孩子送给福利院,他那时经常参加长沙市老干局“关青工委”的活动。我妈说,你关心别人的下一代,还不如关心自己的下一代。于是,那孩子就留了下来,我妈还给他取了名字,叫毛毛。但我从来不让毛毛叫我爸爸,毛毛管我叫叔叔。酋长说,毛叔叔,你好厉害呀!我说,酋长,你欠扁! 军训结束时,是国庆节前夕,学校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分列式。我是掌旗员,酋长是两名护旗兵中的一个。我们齐步走在几千名新生的前列,心情却大相径庭。在通过检阅台之前,我下达“正步——走”的口令,并和护旗兵由齐步换正步,同时换端军旗。在劈下军旗的刹那,我斜视检阅台,那里并排站立着大学领导和部队首长。我看见了王支队长,他向军旗敬礼,我觉得他是向我敬礼。我还用眼角的余光,瞥了酋长一眼,发现他迈步非常小心。我在暗中骂道:日老子的酋长,你今天不想威风了吗? 中午,酋长和一帮新生在学府餐厅为我送行。一些同学找我签名,并要我留下联系方式。我还收到了不少礼物,男生送我香烟,匙扣,钱包;女生送我卡通纸,绢花,小熊饰物等。湄沁的上铺是浙江人,大家叫她小胖。小胖送给了我一个香吻,然后“哇”地一声大哭。我有些尴尬,我是一个三岁小男孩的父亲,不知小胖知道后,还会不会吻我?小胖的哭声,感染了其他人,有几个女生抱成一团,开始抽泣,好像不是送我回部队,而是送我赴刑场。 酋长说,咱们四年以后再相见。 酋长的长远规划,令我汗颜。回到中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许大头”递交了一份退役申请。那时,有许多服役期满的士兵不愿意离开部队,想留下来入党、考学,或者选改士官。郝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想报考军校。我不愿意留队,是因为我不想成天看到“许大头”,他让我感到恶心。退役后,我在W市东游西荡。有一天,在八一路,我碰见了郝强。他对我说,老兵离队后,王支队长来中队检查工作,顺便问“许大头”,那个“刺毛”呢?“许大头”说,退伍了。王支队长没有吱声,转了一圈就上车回了机关。听郝强这么一说,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王支队长是个难得的正直的好干部,他对我有好感。但那又能怎样呢?我对部队没有好感。 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做生意的门点,手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后来,我就碰到了沫沫。沫沫和我一样,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她的生存手段比我高明。我从来没有问过她是哪里人,是做什么的。但我明显感到,她就是W市人,什么事也没做。沫沫整天上网,有时彻夜不归。我生气的时候,就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但沫沫总可以坐在楼下的小餐馆里,让刚刚认识的网友埋单,并顺便给我带回一提盒饭。沫沫只和我一个人做爱,她需要很黑很黑的环境,在黑暗中花样翻新。我很反感,拉亮电灯,沫沫就紧张,哭闹。沫沫还经常拿我的钱,偷偷买彩票,她以为我是傻瓜,把那些打印的小纸片藏在胸罩里。其实,沫沫才是一个大傻瓜。 百无是处的沫沫就一样好处,她特别喜欢小孩子。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车上,只要看到别的年轻夫妇牵着自己的孩子,不管认识不认识的,沫沫总要上前去和那孩子打招呼,并掏出一块口香糖什么的逗那孩子玩,搞得一对年轻的夫妇紧张得不行,以为沫沫是拐骗儿童的人贩子。住在沙奶奶附近的邻居,更是深受其害,五岁以下的小男孩、小女孩全都被沫沫“拐骗”过。时间一长,邻居们也习惯了,“拐骗”总归是“拐骗”,那些孩子认生,长的个把小时,短的三五分钟,孩子们吃完沫沫的东西后,不是吵着要自己回家,就是被他们的父母找上门来接走。这个时候,沫沫总是泪眼涟涟,一副伤心不已的痛苦相,反倒像是别人的父母,拐走了她的亲生儿女! 1999年春季,大学开学后不久,小胖来找过我。她见我和沫沫在一起,很是为我惋惜了一番,她同时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湄沁和酋长被学校双双开除了。我很惊讶,他们还是大一新生。 小胖说,湄沁寸步不离酋长。有一次,他们躲在蚊帐里做爱,被查房的辅导员逮了个正着。学校有规定,男女生之间发生性行为者,发现一个开除一个。学校经过调查,发现他们并非第一次。湄沁总是趁着宿舍管理员不注意,偷偷溜进男生寝室,然后一头钻进酋长的蚊帐里不出来。管理员没看见也就罢了,可他们偏偏要在深更半夜,弄出一阵不大不小的声音来,把同寝室的另外几个男生,搞得心旌摇荡,彻夜难眠。就这样,一群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夜夜凝神屏息,天天无精打采,饱受了身心煎熬之苦,时间一长,他们个个都萎靡不振。实在是受不了啦,几个同学一合计,集体上辅导员那儿去告密。湄沁的父亲是省直部门的副厅长,他让湄沁离开酋长,然后送她去另外一所大学。结果,湄沁从自家的两层小楼上跳下来,摔断了胳膊。气急败坏的邱副厅长,也就是湄沁的父亲,腾出泰格公寓的这套空置的房子,给了湄沁。他说,你就跟那小子结婚吧。 我找小胖要了湄沁的电话,湄沁证实了小胖的说法。她满不在乎地说,这样很好!我可以坐在自己的家里,自由自在地看书复习,争取明年再考,考外地的大学。我说,酋长今年二十一岁了,他考过三次,他可没有你那么多的机遇。湄沁说,那有什么,反正他也不喜欢他现在的专业。我问,那酋长打算怎么办?湄沁回答,他在路灯局做临时电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宁愿把酋长当作一名“电器工程师”,而不愿把他看成是一个电工。如果不是碰上湄沁,将来的酋长,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和酋长做朋友,我非常愿意。问题是,酋长有些清高自大,他表面上认同我这个老乡,也表示愿意和我做朋友,其实他在内心里,根本瞧不起我。酋长这人,骨子阴得很!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一般都是胸怀大志、藏而不露的人!他们平时绝对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就像一条正在修炼的草蛇,潜伏山洞五百年,只待时机。时机一到,它就会打一声呵欠,然后飞身而出,一举成仙! 在酋长还没有成仙之前,天赐良机,让我有了刺探他内心的机会。我现在就要打开酋长的日记。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湄沁的声音:“你睡了吗?日记看了吗?” 我说:“没有。” 她说:“什么没有?” 我说:“什么都没有。” 湄沁在笑。“不要看了,酋长回来了。” 我很生气,觉得被湄沁戏弄。我问她:“那酋长昨晚干吗去了?” 湄沁转述酋长的话:“他只不过是陪他们的局长下了一通宵象棋。” 我又问:“那酋长现在干吗?” 湄沁说:“睡得像一头死猪!”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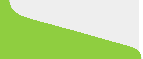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9898-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