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旧梦:记忆中的竹溪镇 |
|---|
| http://y.sina.com.cn 2004年03月26日 13:37 《青年文学·下半月版》 |
|
多年来,竹溪镇一直盘桓在我的心头。它初春的杨花和秋末的落叶,它青苔的湿润和石板的光滑,常常在寂寥时,不期而至。像是潮湿的野地里突然打开的一道大门,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和美感。 竹溪一年里有大半的日子与雨有关。在雨天,竹溪的人都是统一的打扮:竹笠、蓑衣。竹溪人固执而骄傲地沿用这种雨具,于是我就不只一次地听到镇头杂货铺的黄牙四伯喋喋不休地抱怨,他批发回来的雨伞要让他亏老本了。 竹溪镇一面靠山,三面环水,四伯的杂货铺就在竹溪通向县城的路口上,很是金贵。四伯的家同样是两层的木房,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店铺。店铺的大门,刷着一种只有劣质的油漆才能呈现出来的晦暗的朱红色。竹溪人只用桐油刷房子,一则驱虫去虱,二来美观大方。被桐油涂过的木房,在太阳下都发出一种黑金般的明亮的光来。 四伯的头和桐油房子一样光亮。他是个秃顶,不爱说话,但一开口就唾沫横飞,让人一下子就清楚地看到他那两颗招牌式的黄牙。四伯的杂货铺是这样布局的:一进门左边,是三排用木板钉成的简易的货架,上面堆满了红、白、绿纸和草纸卷。正对门的是一个镶有玻璃拉门的红木货柜,里面趾高气昂的陈列着一些包装俗气色彩鲜艳的白酒和汽酒。据说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不过这个说法由于我个子还过于矮小最终未能被证实。货柜前面是一个玻璃柜台,柜台上的几只大塑料罐里装满了大白兔奶糖和五颜六色的水果糖。柜台里面放着几包烟,我最早知道的汉字就是从烟壳上认识的,比如“游泳”,比如“家园”。右边的空地上放了几只硕大的酒缸,里面是烧酒,五毛钱就用酒升量一大杯,三毛钱一小杯。四伯的杂货铺并不是整天都开的,只有在傍晚时分,那扇暗红的大门才“吱呀”一声打开,四伯光亮的头从里面显现出来,竹溪的人就知道,四伯从田里回来,杂货铺要开始营业了。杂货铺的酱油味、糖果味、米酒味四散开来,使得只吃青菜萝卜的人家就着这香味,也多吃了半碗饭。 竹溪镇上的人都种菜,竹溪依山傍水,浇菜种地都很方便。萝卜、青菜、茄子、南瓜……一年四季总离不开这些。卖菜是不用愁的,一大清早,太阳还没有出山,就已经有七八辆收菜的拖拉机停在镇头的车站,挑过去,两方讲好价钱,过秤。一日清闲。 竹溪镇上水田都是按照人头平均分配的,至于种菜的菜园,却需要自己去山脚下垦荒。四伯不愿意去垦荒,于是就只有掏钱去买菜。清晨出菜的时候,四伯就跑到门口,拦住挑菜经过的女人:“细妹,分一把白菜给我吧,多少钱?”女人就说,都是乡亲,四伯拿一把去吃便是,不要钱。四伯也不客气,拿了就走。久而久之,卖菜的女人就不愿意再送了。四伯就掏钱买。买一棵白菜或是几个萝卜得花上一柱香挑拣,然后压价。于是卖菜的女人又不愿意卖给四伯了。 我曾经在捉迷藏的时候,很偶然地窥视过四伯家的厨房。那是我见到过的最简单的厨房之一。一个土灶、一口锅、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碗形单影只的煮白菜。厨房里有一股类似馊米饭和久泡衣服的古怪气味。这是一种很难详加描述的气味,像是深山老林里的毒瘴,又像是久无人居的废墟里积蓄的霉气。这种特别的气味一直弥漫在厨房里。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这是暮年的气息,独身老人的房子就会有这种气息。 杂货铺的对面就是小学。教学楼的长廊上,密密麻麻地摆放着种有凤仙花的花盆,一层粉白,一层鲜红。它们旗帜鲜明地挺立在青色教学楼不同的楼层上,迎风招展,美艳绝伦。放学的时候,当天的值日生就会拿出一个喷壶,轻轻地为它们洒上水。多年来,这样一个甜蜜亲切的、无声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疯长,美丽的凤仙花在甘霖里吐蕊争芳,徐徐开放。 对浇花的渴望一度让我把镇上的孩子分为两类:一类是上学的孩子,一类是不上学的孩子。前者可以拿上各色的课本去小学里上课,每天值日的时候去浇花,不用打猪草、挑水。而后者要天天卖菜、喂猪,要会看秤,要会说脏话,不能参加运动会也不能拿喷壶浇花。而我正好被我自己制定的标准划分到了后者。具体我是如何从“不上学的孩子”跳入另一个范畴之内的过程,我已经很模糊了,去小学参加趣味运动会和拿喷壶浇花的喜悦掩盖了其他一切无关大局的细节。我曾向阿妈求证过十二年前班主任踏入我家木屋之后的所有情节,阿妈竟然也只搜寻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和声音。 在我9岁的那年,班主任的丈夫调到竹溪小学当了校长。这一年,我们镇上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黄牙四伯。 班主任在小学里盖了一间校园小卖部,墙上挂出一排花花绿绿装裱得很好的纸片。她的店里有很多好玩又很便宜的玩具。比如溜溜球,比如七巧板,比如变形金刚。还有一毛钱两毛钱一包的七彩糖豆、酸梅粉、橡皮糖。还有小人书出租,两毛钱可以看四本。我们渐渐地就都不去黄牙四伯的杂货铺了。接着大人们也不去了。在班主任的小卖部里可以赊帐,在四伯那却非得现钱现货。四伯突然就更老了。经过四伯的杂货铺,我莫名地心惊肉跳起来,屏住呼吸飞一般地冲过去,然后跑进教室里才大口大口地喘气。 有一天,天有些阴,县里工商所的人下来,查抄了四伯的杂货铺。人们传说着那是因为四伯没有给他们“上香”,但更体面的说法是四伯没有班主任店里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我们小孩子都不明白为什么纸片在查抄事件里举足轻重。大人们解释说没有营业执照是不合法的。 我的黄牙四伯在那个微凉的春天里独自坐到了傍晚。那个春天的傍晚像极了秋天。寒风贴着地皮隐隐地扑来,潮湿的青石板被吹得干白干白的,竹叶发出沙啦沙啦的响声,河水呜咽着向远方滑去。黄牙四伯在这样的傍晚伏下身去。 后来风停了。黄牙四伯就向着河边走去。有一枚湿湿的圆圆的月亮躺在河心,偶尔扭动一下身子,像是在发出某种暗语,成片成片的凤仙花诱人地挺立着,泡桐树在河滩上做着美妙的梦。在这个夜晚,有月光,有河,有花,有沙滩,没有人,又干净又美。于是他就在这个夜晚消失了。 黄牙四伯投水后,我才想起来问阿妈,黄牙四伯跟我家到底什么关系。我阿妈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四伯跟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并不是谁的四伯。四伯的墓我远远地见过,窄窄的小小的坟头,是竹溪人看去极为寒酸的那种。墓碑上没有子孙的名字,连他自己的姓名,也都只有“黄牙四伯”四个字而已。它们显得那么突兀、孤独、烦躁和不安。 另外一个,就是冬冬。冬冬是班主任的孩子,他爸爸是我们的校长、班主任的丈夫。冬冬这一年9岁,是我的班长,学习很好。他的名字让人联想到一种打鼓的时候才发出的声音,叫起来有一种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感觉。冬冬是竹溪镇上最整洁的男孩子,他有一件棱角分明的白色衬衣。冬冬还有一架电子琴。在1991年的竹溪镇,电子琴是非常罕见的东西。冬冬弹得很不错。有演出的时候,冬冬的电子琴独奏总是保留节目。 在竹溪,小学每个学期都会放一个星期的农忙假,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各自回家帮忙插秧,我们最忙的时候也是冬冬最忙的时候。顾校长和班主任很少在学校里露面了,整日不见踪影。冬冬后来告诉我说,那是他们在家辅导他的功课。他很烦。 那个中午,冬冬的烦恼达到了极点。不过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所以事先,他没有流露出任何出逃的蛛丝马迹。否则顾校长和班主任也不会在那样炎热的中午沉沉睡去。冬冬偷偷系紧了那双轻易不穿的白色球鞋,从临河的窗户里,猛地跳了下来。他笨重地摔倒在裸露的河滩上,又迅速地爬起来,歪歪斜斜地向稻田跑去。 当时,我正在河边洗脚,冬冬像一只小兽般窜过小桥。我听到一阵迫不及待的脚步声。我抬起头,看见冬冬快活地向河这边广阔的稻田奔来,他跑来的时候正好背对着阳光,他的面孔便有些模糊,仿佛有一团阴影笼罩了他。我只看到他瘦瘦的个子外的一圈光晕毛茸茸的,很柔和。 我听到冬冬说话了:“你带我去稻田吧。” 于是我们来到田野。我们看到了青翠欲滴的稻秧,阳光在叶尖上跳动。我们看着稻田,望着稻秧,然后心一横,“噗嗵”一声跳下去插秧。我们左手拉动一捆稻秧,往后退,右手紧握一兜,使劲往泥水里插。我们看见稻秧像做广播体操的学生一样整齐划一地排列起来,我们就很开心,但是我们很快就又紧张起来。我们被蚂蝗叮了。在水田里,无论迟早,左脚或者右脚,总会附着上几条肥硕的蚂蝗。冬冬的腿僵硬在半空中,他的额头隐隐有青筋暴出。我淌过去,捡起一片竹篾,极快地从上往下一刮,蚂蝗就缩成一团,滚落到泥水里去了。我们心惊肉跳地蹦上田埂,然后心有余悸地笑起来。 冬冬穿着洁白的短袖衬衣,微笑着,腼腆而干净。他站在开满黄色野花的田埂上,旁边是沾了污泥的白色球鞋,耀眼的天空湛蓝广大,天地间布满了均匀纯净的蓝色光泽,一错眼就会看到临河的半边也全是蓝色的花朵,另外半边,半滩艳红的凤仙花灿烂地燃烧着,极为奇特。楠木河亮晶晶地流淌,水稻清香的气息缭绕其中。 接着到来的就是炎热的夏季。1991年的夏天来得很早,热得出奇。这对于竹溪的孩子来说却并非一种灾难。脱得光溜溜的孩子们名正言顺地在河滩上打滚,全身沾满野草的碎屑和沙土的微粒,黑黝黝的皮肤上有一种直接来自太阳的光芒。大一点的女孩子们在河的上游嬉戏,冰冰凉滑呼呼的河水刺激得她们大呼小叫。男孩子们从下游的河岸上猛地扎入水中,溅起白色透明的水柱。但是这样美好的河滩被班主任误认为有锋利的铁钉、破碎的瓷片和尖锐的石头,所以冬冬从来不曾被允许上河滩玩耍,也未曾游过泳。我们玩水的时候,他总会出现在临河的窗口看,一站就是半天。 有一天下午热极了。河滩上的树木蔫得像一层扁扁平平又焦又脆的烟壳锡箔纸。男孩、女孩、男人、女人就都煮饺子似的泡进河水里。 冬冬再次从临河的窗口跳出来的,他光着上身,欢快地跳进河水里。他离开人群拥挤的河段向着更远的地方走去。大人们发出了警告:“冬冬,快回来,那边有‘锅底’嘞!”不知道是大人的叫声太小,还是距离太远,抑或是冬冬压根儿就没听进去,总之,冬冬执着地、一如既往地向着人迹罕至的水域走去。水越来越深,最后,他的身子在水面晃了晃,就沉溺不见了。 那个黄昏。淡青色的天空突然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玫瑰色的云彩,它孤零零地浮在那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班主任凄厉的声音在的河滩上回荡了很久,河水被搅得一振一振,凤仙花的花瓣落了一地。 这是我迁离竹溪以前所记住的最后的画面。 我重新踏上竹溪新铺的柏油马路,是十二年后。 老房子在拆迁,空气里充斥着粉尘的颗粒。饭馆的伙计搭着油腻腻的大褂,懒洋洋地倚在尘土飞扬的门口招徕客人。马路被拓宽,挖开的地方坑坑洼洼震得人肝胆俱裂。路口的大超市里放着震天响的流行歌曲,呛人的声浪鞭子狠狠地抽打着并不坚强的耳膜。楠木河上修建了新式的大桥,4个浑圆的桥墩气派地矗立在水中,风雨桥全无踪影。四伯的杂货铺甚至都找不到它原来的地基。小学正是放假的时候,青色的砖楼已经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是一幢现代化的教学楼,镶着白色的马赛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去小卖部买巧克力豆的时候,卖东西的小姑娘很不乐意地递过来一包,顺手接过我的两毛钱,看也不看就扔进了钱盒。宣传橱窗里贴着现任校长的照片,姓李。看来班主任和顾校长早就离开了。 我嚼着巧克力豆,走到那条柔软的河流旁边。这里已经开辟了沿河花园,种了草坪和一串红。现在是夏季,温暖的阳光打在光滑的河面上。空气湿润而清新,楠木河依然和当年一样丰盈。世界上的水周而复始,彼此相通,某一地的水经过一定时间的循环,会到达另一地,然后再回来。我不知道十二年前的楠木河水是否再次流经过这里。我只看到河面上漂浮着许多凤仙花的花瓣,既虚空,又富有质感。北半球的阳光射入我的眼里,它们是那样刺鼻和辛辣,让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记忆中的竹溪永远是个梦,于流年里彷徨,因靠近而褪色,在接触中破碎…… 文/欧阳琴娜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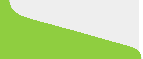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