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刻天涯:右手,与幸福擦边 |
|---|
| http://y.sina.com.cn 2004年03月10日 10:45 榕树下 |
|
恭喜你,签证这么快就办下来了。同事伸出手。 握手是一种礼节。我伸出右手,没有犹豫,但,勉强。我只是不喜欢这种礼节。 机械地笑、机械地握着一双纷纷伸过来的手,手的表温掩饰不了背后的冷冰。 我去打电话。晃了晃手机,与虚应的热闹中脱离。摘下微笑的面具,只剩一张疲惫的皮囊。 电话,没有可拔的号码。 右手,还残留着礼节的触感。我不是虔诚佛徒,没有右手比左手晦污的岐视,不喜欢握手,是因为害怕,害怕哪一日重复冰冷的节奏会覆盖被他轻轻拉着的温暖………… 那年,普通冬日,中午,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课代表,来准备幻灯片。教室里空荡荡的,映射布上有灰尘。搬凳子去擦,不小心,手镯上的铃铛被挂住,弹落,滚到门口。跳下,走过去。一阵酒气,皱了皱鼻子,一个说不上熟悉也不能说陌生的人,同班同学,问题人物,局子里的常客。 谢谢。从他手中接过铃铛,银是导热的,铃铛上微微带着他的手温。 我甚至没有抬眼,转身,手却被绊住了,是?我扭头,是他的手!惊慌! 你不知道吗?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幽凉,不知怎的有一种凄然在我的心里慢慢蔓延。你真的不知道吗? 他的眼睛红红的,越来越红,眼中的幽凉渐渐泛滥,终于,涌出,划过深沉的轮廓,滴落在我手上,被他握着的右手,皮肤像被灼伤,疼,心狠狠地抽。 静怡!我如梦初醒,教室后门边站满了同学。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用力甩开一种缠绕在心上的感觉。 我什么都不知道。跟他说,也跟自己说,飞步走开。骗他也骗自己。我读通宿,每天晚自习,背后有人,一直送到我家楼下,那人,是他…………
嘀嗒——嘀嗒——手机响起,是彦,享有富有名望的姓氏,我的未婚夫。中午吃饭,法国菜。 这几天你就在家好好休息,需要的东西列个单子,交给我。彦笑着看着我。那笑是一种说不出的骄傲与成就感的结晶体。 没什么要准备的。 翻开菜单,每位最低消费在我工资的三分之一以上,不过,五位数以下彦都不会有什么感觉。如果,只是如果,坐在对面的是他呢?不,如果是他,此刻大约在某条小巷的粉摊上。听说,毕业后半年多,通过一个在什么地方当科长的伯父进了一家工厂,当了工人。 这是我和彦第十七次到这间餐厅,一二三,顺着菜单数到十七,就这个吧! 你不是不吃胡萝卜么?彦看着我。 无所谓。 望向窗外。下雨了,雨丝斜斜密密地缝在行人的衣上,把颜色弄得更深沉了。 盘子端上来,银制的,镂刻着花边,我伸手,手上的铃铛碰着盘沿,清脆的声音竟有些许悠远。 不喜欢我上次给你买的玉镯么。老坑玻璃种,确实漂亮。 不是,带惯了。 看着盘里红红绿绿的胡萝卜和豌豆,颜色很漂亮,但,眉头在收拧。 麻烦给我一杯水。我对服务生说。 和着水咽下我的无所谓。 走出餐厅,雨小了,朦朦的,前面好像笼着一层层薄纱,怎么也挑不破、拉不开。 服务生把车开过来,我想说我想走回去,彦已打开了车门,望着我。
公司那边有什么不妥吗?彦问。 没有。彦家里早已跟老总打过招呼。 病了么?彦伸出手摸摸我的额头,我不由自主往边上一偏,惚了一下,觉得不好。 你在开车呢。我努力让嘴角向上,弯下眉毛,对他笑了笑。 回去好好睡一觉。彦轻轻握起我的手。 嗯。闭上眼,脸朝右,身子向下动了动,调整坐姿,手从他手中滑落开,自然滑落。 车窗没有摇紧,有雨不时地飘进来,落在脸上,凉凉的——车停了。我睁开眼,还在路上。 可能是油路出了点问题。彦走下车去。 我打开门,跟下去。雨很轻,但只一会儿,就给每一根头发沾上了湿意。 那一天也是这样的雨,轻轻的、密密的,只是在夜里,是圣诞。系里开parrty,怕太晚,我提前离开,悄悄地。静静地路上只有风声、雨丝、零零落落陌生的路人,和我。 静怡!谁?我的心跳到嗓眼!惊恐地站住!转过头! 是他!借着幽幽明明地路灯,我看见一张苍白腼怯的脸。他,显然也看见我的惊慌。 别,别怕。不知是寒意冻的,还是感染了我的不安,他的声音在抖。 给我一分钟,就一分钟。他哆嗦着从口袋拿出一个信封,一个鼓鼓地信封,递了过来。 我没有接,不敢接,心绷成不能更紧的弦,他又喝酒了,酒气在四周慢慢散开。 他拉起我的手,我的右手,好像很久,又好像只是十几秒钟,把信封放在我手里,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信封,轻轻一动,发出嗞嗞地声音,不会是炸弹吧!我迅速将它扔开,向前跑。 没有响,没有任何动静,回头,白色的信封在黯淡地光线下清晰得刺眼。 迟疑,还是走回去,俯身,拾起,泥水已噬透白色的纸。 打开,一张卡片,还有,一只发夹,水晶的,纯白水晶的发夹。 我愿做你的发夹永远陪在你身后。字很漂亮,不像他这种人写的。 发夹,我不自觉地摸摸快垂到腰间的长发。 静怡,静怡。 我回过神,彦疑惑地看着我。 真该换了。彦飞起一脚踢在车上,车身留下一个和着泥水的脚印,水流散,脚印慢慢扭曲。这车是去年春季车展上订购的。 彦拔通修理厂的电话,一会儿来人。 我给你打个车,你先回去。彦看了看只穿着一件衬衣的我。 这里是环线,哪有车。彦的眉头拧得有点挤:你先到车里去,我打给家里的司机。 我没有搭言,也没回车里。既然湿了,就彻底湿透吧! 第四十五辆车开过,第四十六辆停下,修理厂的。 怎么样?彦敲出两支烟扔给修理工。 要到车下看一看。话还在空中,人已钻到车底,连张纸都没铺,路面上的水已可溅起水花。 我忽然想起他,他在的那个工厂好像也与汽车有关。如今他也像这修理工一样么? 修理工从车下出来,一身泥水:好了。 我看着修理工的手,指甲缝还有手指、掌心的每一条纹路被黑色的油污填充,填的很深很现,像一条条小小的沟壑,好像永远也洗不掉、抹不去。 那就是干这活的人的手。彦在我耳边说,声音不大不小。我看见那双黑黑的手向里抽动了一下。 谢谢!我忽然走上前去,伸出手——向修理工——向那双沾满油垢的手。 修理工吃惊的看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摊开手,示意手上的污渍,雨水打落,油垢散开,淡出彩色的油星。 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丝勉强,我迎过去,紧紧地握住了那双手。紧紧地,重重地,我知道,我是在握他的手,是在握那一双手………… 春游,江面,游船,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和我在一条船上。 同学们坐在船栏上,用手敲动水面,撩起涟漪。我晕水,躲在船舱。 禁不住同学欢呼和美丽波纹的诱惑,我也走了出去。 俯身,伸出手,水中的我在笑,笑的很灿烂,灿烂,灿烂在扭曲,扭曲,我的身体不能动弹,呼吸在渐渐被遗忘,从颈到肩到指尖知觉一点点麻木。最后一丝意识:再这样,我会以这样的姿势倒进水里。 静怡!耳朵忽然被尖叫、慌乱的脚步声塞满,冰浸的水在我身边忽高忽低,我喝下第一口江水,身体在不由自主的沉浮,我想站起来,但这不是地面,我的知觉仍在继续流失,甚至失去声音。 忽然,身体停止下沉,手,手被紧紧的抓住,传递过一股力量在把我往上拽,在与水争取。 那是他的手,是他,他紧张的眼神、他咬紧的牙关。那被强力拉扯的手臂上有一些鲜红的东西在沿着暴突的青筋流下,顺着他紧紧拽着我的手指流到我的手上。我眼前,只有涌动的江水,鲜红的水——我醒来,不知是多久以后的事,他的手还紧紧握着我的右手,伤口尚未淤结。 你没事吧!旁边有很多声音,但我只听见了他这句话。 这句话刺在我的手上、刺在我的心上,一阵酸楚在我慢慢恢复的知觉中显现,很冷,很冷,是江水,是江水在衣服里肆意地抢夺我的体温。 我抽出手,从他的手中,捂住眼晴,虽然我知道没人能分清眼泪与江水………… 静怡,静怡。彦递过一张纸巾。 我愣了愣,把手放到鼻尖,一股汽油味刺激鼻息,这就是他现在的味道么? 静怡,静怡!彦的声音高起来:你今天总是走神。 对不起。接过纸巾,没有擦,团在左手里,捏紧,捏灭一种念头。 静怡。彦靠过来,拔弄我坠在项链上的戒指,订婚戒:记住,你的手是要用来戴上它的。
彦没有坚持送我上楼,进家门,却听见妈妈在讲电话:她上来了,好,好的,你开车也要小心! 你病了么?妈妈挂断电话,不用说是彦的。 没有,就是累了。给妈妈一个微笑,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关上了门,眼泪却打开了………… 那晚,我在学生会轮值,时钟敲过九点,我正准备关门。一个一年级的新生慌慌张张地跑来:树林,树林那边有人在打架,动刀了! 没想起那种叫勇气的东西,也没细想那些渐渐凸现的惧怕,我叫新生去找保卫科。,一个人跑向树林。 金属和金属碰撞的声音、金属与身体碰撞的声音、身体与身体碰撞的声音。我的脚在抖。 你来这干什么!快走!我的手被人拉了一下,是他,手心满是汗,不知是我的还是他的。 你!你——我早该想到这样的场合一定会碰到他。 快走,快离开这!他焦急的看着我,而我只是冷冷地盯着,盯着他的焦急。 灯光四射,保卫科的人来了,警笛声在临近。 树林里的人被带走了,他也被走了。 十天拘留。 第二天,他寝室的人问我:几点出的事,九点一十他还在寝室门口晾衣服,有人来找他说了什么就出去了。说什么没听清,只隐约听见有我的名字。 我?我——学校里,几乎所有知道我和他的人都在议论,老师、同学甚至我爸妈。 你跟他倒有没有那回事。爸爸用从未严厉目光看着我。 没有。我无法想像有的话,家的这份安宁会变成什么样子,而我不能失去这份安宁。 没有。他也是这样跟学校说的。打架斗殴,记大过,留校察看。 一天、二天,在一种叫心神不定的煎熬中熬过了九天,看见他,苍白的脸。 你是不是去打架的?我问他,声音有些颤,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要怎样的答案。 他看着我,很久,既不点头也没摇头。 为什么?我的手攥的很紧,关节快要从皮下跳出。 你不知道?你还是不知道?他看着我,还是那么幽凉的目光。不知道也好!我这种人——不知道是多久,熄灯哨响起。 能让我再握一握你的手么?他伸出手,他的手在抖,我的心在抖。 我转过身,背向他,彻底背向他,走开,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摆脱某种关系,摆脱与他有关的任何关系…………
倒在床上,一分钟、五分钟、半个小时,柔软的被子裹不住我纷纷乱乱的思绪,坐起来,打开书柜,挪开最底层外面垒着的一叠书,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的地方。 拿出匣子,一个红色的铁匣,上面有圣诞老人、牝鹿、彩带和雪撬,小时候,爸爸送我的泡泡糖的盒子。 打开,里面有六个本子,我六年的日记。拿出倒数第一本和倒数三本。 按上房门的反锁。 抚着日记本发黄的侧页,额头贴着封面,摩擦可以生热,可额头与纸张却怎么也擦不出暖流。脑子里有一些东西在流失,我在等,等流失干净,完全空下来。 翻开倒数第一本日记的封底,轻轻抽出硬纸片,从皮夹层,拿出一封信,一封永远不会发出的信。我给他的信,六年前,我彻底背向他那天晚上写的信。没有称谓,没有落款,只有三句话: 你我只是风中飘零的落叶, 偶尔的重合, 只是风向的错误。 抬起头,用力抬起,终于体会水在杯中要溢出的感受,如我的眼,如我的心。 握紧倒数第三本日记,在它的封底躺着还有一封——第二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不用打开,那上面的每个字、每一个笔画当初是怎样落在纸上的都已刻进了心里: 分离,却不是结束; 重逢,却不能相守。 日期是三年前,夏天,同学琼的婚礼。我知道会遇见他,连招呼的台词都想好:好久不见。 酒店外,迎宾的新娘花枝招展,看见我却一脸肃然我拉到边上:他刚进去,还有一个女孩,挽着他。 那又怎样。嘴比心坚强,但这坚强却毕竟是柔软的。我往里面一瞥,他正在旋转楼梯的转弯处,四目交接,一刹那,我知道我必须走,离开。 把红包塞在新娘手里,转身,从未有过的步速,拦车,逃跑。 关上车门的瞬间,他从酒店里冲出来,目光急切地搜索,胸膛急剧地起伏。倒车,我从他身边离开,我突然笑了,后视镜里的我从容得多,从容得冷酷…………… 睫毛和枕巾间有些东西冷冷地浸着我的感觉。我站起来,头有些晕。 把日记重新放回匣里。右手拿起我的信,打开门,走到客厅。 爸,妈。 爸妈抬起头看了看我。 饿了么,要吃点什么吗?妈妈问。 不用。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食物了。 爸妈的目光重新转回电视。 我走到他们面前,走得很近。他们都有很好的视力。我站着,眼睛看着电视,画面一个一个闪动,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我的右手在抖。 爸,你的打火机在哪?我大声的问,很大声。 爸爸递给我,目光在我的右手上停留了几秒:快没气了,你多打几次。 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比秒针更快,我深吸了一口气,昂起头,腰挺得直直的,走进浴室。关上门,所有力气一下全部消失,倚着冷冷地墙壁瘫坐下去,地上有水,我知道。 我已经在爸妈的面前,在除了我以外的别人面前亮出过这份心情了。 落叶也好,飘零也罢,一点火光,过去永远过去! 打开水笼头、打开换气扇,最后一丝痕迹完全消失…………
晚饭,彦过来了。 明天开始准备行李,我订了下周的机票,好吗?彦看着我,眼神中并没有征询的意思,‘好吗’只是个后缀。 我点点头。 明晚,有几个朋友要给我们饯行,你想吃什么? 中国菜,湘、鲁、淮、扬随便。 是啊,到外边就吃不着了。妈妈的声音忽然感伤起来。 母亲的心就是这样,孩子就像是手里的风筝,希望飞得高飞得远,却总有一根舍不得放不下的线头在牢牢握在手中。 我轻轻摇了摇妈妈的肩,跟妈妈笑了笑。
像长条吐司一样的大客车,蓝白相间的车身,他在开车,我在卖票。清辙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方向盘上,照在他手上,他回过头来有说有笑……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停停开开。我站在车门边,倚着车窗笑得很轻松。不知道开过什么地方,只知道我们要去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在哪?我不问,反正高高兴兴…………… 静怡,静怡,起来了。妈妈在敲门。渐渐清醒,只是一场梦。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一动不动,不知要干什么,也不知倒底想干什么。 上午清东西。平时看上去空荡荡的房间收拾起来,好像什么东西就都跑出来了。 你就是什么东西都喜欢收着。妈妈拿着一条辫子。 那是我二年前剪下的头发,原来绑得很紧,现在失去发根的给养,变得松松的,好像一不小心就会从发绳中溜出来。 我靠近去,轻轻地抚摸,虽然已不再光滑。 这是什么?水晶、纯白水晶的发夹,他送我的发夹! 妈!这是什么?我明明把它扔了,那天,二年前,琼婚礼那天,那天是我和彦确定关系的日子。 我怎么知道?妈妈诧异地看着我的反应。 没,没什么。谁,谁还戴这么老土的东西。笑,不敢看妈妈,笑比哭更难。 我以为我把它丢了,却不知它一直都还在,就在我身边。 瞄准垃圾桶,扔,没中,碰到桶沿,弹开,竟落在旁边的行李箱上。 这——我的心狠狠地抽了一下。冲过去,用力捡起,用力摔进桶里。 装作若无其事,继续整理。手中的琉璃风铃放到左边又放到右边,放到上面又拿下来,到底放在哪好?扔,一阵悉悉唢唢破碎的声音,无辜而无奈。 静怡,你怎么了?妈妈拉拉我的衣袖。 我的嘴唇动了几下,就是说不出口,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良久,我轻轻的靠在妈妈肩头:妈妈,你爱爸爸么? 怎么问这个——两个人过一辈子,怎么能没有感情,这感情从哪来呢?从爱情、从孩子、从事业、从责任。不是单一的一个方面,更不可能依靠单一的一个方面。 说到底,爱情是不能没有面包的,面包是不能没有黄油的,黄油是要钱才能买到的。我怎么问这个,怎么会问这个?糊涂了,真是糊涂了。 嘀嗒——嘀嗒——。接通手机,彦在楼下等我,想起是彦朋友的饭局。 我没有数着星星吃饭的偏好,彦也没有那份浪漫,但彦却一直喜欢在顶楼的天台吃饭,说高且富有整个天空。 我不知彦是否真的拥有想要得到的那种感觉,我只觉得,当清风徐来,我的灵魂就如同风中的轻尘,随时可能被夹带飘离,然后在某一处重重落下,或在看不见的真空,窒息、毁灭。 彦一一介绍着这个、那个。我机械的打着招呼,没有犹豫但勉强地握着手。 彦的朋友都和一些熟悉的品牌、熟悉的名称联系在一起。我忽然记起我对面那个做网站的,那网站我好像曾去过,后来把密码忘了。 我给你一把万能钥匙。彦的朋友在餐巾纸上写下一组数字。有些网站和软件设计时都有这样的后门。 接过,轻轻叠起。 觥筹交错,我不会喝酒,是局外人。 回到家,凌晨一点一十分,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很想睡着,很想,他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啊? 翻来,覆去,时针敲过第二个准点,我起来,习惯性地揉揉眼,其实并无睡意。 外面很黑,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夜,夜是安静的。 打开电脑,网速很慢,想起同事曾开玩笑:深夜里,网路上的人与马路上的人成反比。 点击网站,输入用户名。在衣袋里找出那张纸,餐巾纸生性是柔软地,无论怎样小心叠起,都会皱皱的。输入密码,顺利进入。系统显示:您上次访问的时间是1998年7月26日,四年多了,今天已经是二00三了。 我的班级——通讯录——看见自己的名字,在最前面,我还是这个班级的创始人之一,手指滑动滚轮,他!他的名字!他的手机!他来过这里! 拿出手机,一三九……我记这号码干什么,我又不找他,删除。不,如果他找我,他打给我,手机上就能有显示,我就能有准备,就不会慌张,重新输入。不,他不会找我,他已来过了,应该看到了我的资料,如果要找我,早找了,早找了!删除。不,万一,万一…………… 班级留言簿,按时间顺序。 …………… 王锵到西藏去了! 廖芸你死到哪里去了! …………… 琼要结婚了! …………… 能握着你的手,是我一生的幸福。落款是他,他写的。时间三年前,琼结婚的那天晚上…………… …………… 眼前一黑,UPS刺耳的报警声响起——停电了。 静怡,你在干什么?妈妈在隔壁,被吵醒了。 没,没什么。我急忙关机,关掉UPS.对他来说,只是一句话吧……… 几分钟,备用发电接通,房间重新亮起来。 下个星期我就走了。看与不看,是不是一句话都没什么意义。 关上灯,睡觉。翻来,覆去。数秒钟走动,六十秒,一分钟了,五分钟了。看与不看,都一样,打开灯,打开电脑。 …………… 王锵彻底奉献给藏族人民了,现代版“王氏和亲”。 琼要做妈妈了。 听说了吗,静怡要出国了,跟她那‘四有’未婚夫。 唉!人同命不同,知道他么,他,三年前冬天的时候他那个厂里出事故…………… 他?他的名字,真的,是他的名字! 我猛然站起来,头很晕,眼前一黑…… 有意识,触到一双手,戒指,是妈妈。 妈!妈!换电了吗?又停电了?我什么也看不见…………
俗话也叫雀蒙眼,可能是急虑过度、精神太紧张。好好休息,只是暂时性的。 要听医生的话!妈妈轻抚着我的头发。 我来喂她吃药吧。彦的声音。乖乖吃药才能好得快,才能按时出发,对吗? 彦握住我的手,很紧,仿佛要传递给我些什么,我抬手,将鬓角拨到耳后。 彦,帮我找个号码好么?我把手机给他。叫琼。 琼?要我帮你拔号吗? 我自己来。我摸索着,这是上翻键,这是下翻键,我记得他的号码就在琼的后面。下翻,拔号,挂断。 彦,我想吃桔子,帮我去拿一个行吗? 那你要把药吃了。 听见关门声,打开手机,手在抖,下翻键的旁边是重拔键。 你拔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拔——空号,五脏六腑逐一开始翻腾。心,从未空得如此之彻底。 静怡,你的桔子。怎么还没吃药——你怎么了——是药味太难闻了——好了,好了,不吃了,不吃了。彦着急地说。我去给你倒杯水! 六三六零……,我木然地拿起手机,凭感觉按下琼家里的号码,接通:你好!琼吗?我是静怡,能帮我………………
琼挽着我的手,我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很紧,不想让那些颤动落入任何人眼里。 好久不见!他的声音还是老样子,低低的,夹着一丝腼腆。 好久不见!这句台词已我准备了二年了。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不能改变的也很多,就像我和他相对时能说出来的话,仿佛每一句都准备了几百年,在心里重复了几百遍。 哦,对了,这是我的孩子,还小。不过,不过,会叫阿姨了。来,叫阿姨。 我决定赌一赌,很幸运,伸手就摸到了,小脑袋,短短的头发,是男孩! 你儿子真可爱! 静怡,你,你——我也快有孩子了。我和彦已经办好手续,过去后就要孩子了。 静怡,静怡——我,我们,让我握握你的手好吗?他的声音在颤抖。 好啊!我努力让自己笑的更明朗,伸出我的左手。 怎么了?良久,他的手没有伸过来。我隐隐约约听见一些细细地哽咽。怎么了?我想了想,伸出右手:不好意思,我的右手昨天割伤了! 上面还贴着创可贴。 他的手终于伸过来,他的左手。 在碰到他指尖的一瞬间,冬日、雨夜、树林、转身,全部回来,从时空从心灵的缝隙中偷偷溜回来…………………………… 不记得在意那手是否粗糙,是否有油污的气味,我握住的是依旧温暖的感觉。 没有再见,最不需要的两个字就是再见。 静怡。琼在犹豫:静怡,他,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是个女孩! 泪决堤,无论我怎样昂起头,我以为他不知道。 静怡,你知道吗?他,他没有右手了,那次事故,他…………… 嘴唇和舌尖泛着血腥的味道,他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再握住那只握着我温暧、握着我生命还有幸福的手! 我知道,晚自习后,在我背后送我回家的人,是他! 我知道,他是去树林带我走的! 我知道,他是毫不犹豫地从酒店里冲出来找我了! 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知道,他知道……………… …………………………… ……………………… …………………………… 看见一丝光线………… 看见一些颜色………… 看见一张照片,穿着礼服的彦和穿着婚纱的我………… 看见父母,视频的另一瑞,隔洋隔海,万里之外………… 看见一双手,我的左手、我的右手,我的左手握着分离,分离却不能结束;我的右手握不住重逢,永远不能重逢,永远不能相守,右手,与幸福擦边,永远擦边………………… …………………………… ………………… ………… 文/最爱西红柿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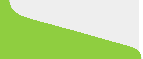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