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都老了吗?--写给《我们仨》 |
|---|
| http://y.sina.com.cn 2005年08月19日 17:33 《青年文学·下半月版》 |
 《我们仨》封面  钱锺书、杨绛及女儿钱瑗 文/宋静茹 对于生命,甜蜜只是况味,并不是实惠。 最近看了几本好书,最先看的最喜欢的,是杨绛的《我们仨》。书分三章: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内里记载着杨绛自己与钱锺书、钱瑗三口之家的点滴往事。如今钱锺书和钱瑗都已作古, 九十二岁的杨绛倾毕生笔力,往事悠悠,写尽三个人的爱恨笑痴。写不尽“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遐思。 这书给我一个印象:生命从诞生到终了,一个人是一辈子,三个人,可以是三种人生,落到一个家里,也还是一辈子。只是有时,对于单一的生命,一辈子漫长辛苦,到头来青春、爱情、欲望都好像精致的玻璃糖纸,层层剥落下去,生命的本质洁白如洗,坚韧朴素,它是个不通明的实体,正面反面,前世今生,写满的没有期盼,惟有回忆。 拿时间码字的书不少,有人专捡个中情味来讲,譬如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也有人专注感悟命运多舛》。这两年市面上的好书愈发少了,杨绛占尽了两种例外。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说:“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趁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杨和钱的女儿钱瑗没有子嗣,她一辈子的身份,就是个天生的女儿,钱瑗是临终时已近花甲,还仍被钱锺书和杨绛当孩童来爱的。在这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钱锺书是快意简单的老顽童,钱瑗是纤细羸弱的小孩子,三个普通人并不普通的人生故事,于是落在杨绛身上。在妻子和母亲双重身份的重势下,杨绛成为天然的,也是惟一的讲述者。 她做得实在优秀!她讲,“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仿若寂寞的魂灵独坐一隅,穿越时光的洪流,安静地注视前世的繁华过往,风起风落,往事零落离散,最后依然一丝丝、一片片地,尽落到这双苍凉的眼里。杨绛此刻看自己,用的便是一双身后的眼睛。一个著作等身的女学者,超越自身价值的经纬,自视为“未亡人”,把自己的生命作为某种附庸——其实是真正悲哀的事!于生活,杨绛心如止水。但不是厌倦,也不是没有希望,看破红尘的弃世。她的心,沉甸甸容量着淳厚的往事,那份沉重直叫人心隐隐作痛,再经不起任何波澜。她的止水,是静水流深的止,不是一潭死水的止,说到底,她的心止,是止于“静”不是止于“死”的。 我其实并不知如何去体会一个老人的心态。我祖父在他最爱的妻子去世后,健康几起几落,生命又绵亘了三十年,这卅载期间,他成为一个极安静极安静的人,很少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对子女亦只是一味沉默地慈爱。但他的姊妹子女,周遭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对我祖母的思念。他保留着祖母给他养成的每晚泡脚的习惯,日日傍晚都喜一个人背着手到铁路边散步,直到他八十岁去世。我和祖父骨血至亲,说到底他对我仍是陌生人。然而,又何尝是对我呢? 如同对祖父的隔膜,今天的我,坐享着馥郁的年轻,便不能把自己换作杨绛,不能真正体会她的心境。我能做的,亦只是热心地冷眼旁观——《我们仨》这书,起起落落翻了几遍,知道作者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一个人,讲三个人的故事,思念三个人的往事,定义三个人的生命。这担子太重,沉郁的情感,一路沉甸甸地奔腾流淌,鲜血梅花一般溅落到读者心上。到我这里不过只是疏疏的几朵,然而,这花却凋落得厉害,竟很快结出涩的果实了!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我是爱杨绛的,也并不全为这本书。我看她《堂·吉坷德》翻译得有趣精到,是羡;看她的《洗澡》、《干校六记》写得深邃坦然,是慕;而时今这本《我们仨》,却只是让我难过。杨绛对我,本是一个很女性的作家。因为绝对的女性,代表着极端隐忍和极端沉着,看她的书,反不必去追随童稚的趣味,一切诙谐幽默皆来得浑厚沉着,自然成就大气!我看她回忆自己的长辈——父亲、姑姑,一样客观理性,不带小儿女的娇痴,天生一股子“端然”的气度。我喜她的从容,把杨绛随便和其他的女性作家相提并论,就不乐意。杨绛的可爱是性情上的,不是文字上的。从性情上来看,她能使我联想起的惟一位作家,却是张爱玲。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里,曾这样写—— 我八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这使我想到张爱玲写在《倾城之恋》里的一段—— 恍惚又是多年前,她还只十来岁的时候,看了戏出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家人挤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似乎是魇住了。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猜着是母亲来了,便竭力定了一定神,不言语。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都是小孩子家的“别一种滋味”,杨和张的感受看似迥异,其实交契。小孩子做得实在无邪,反容易在一个瞬间里,从周围的情景中切割出来,感受到大的人间世故。 杨和张的共同之处是都活得独立、谨慎,把自己和这世界撇得很清,因而有点儿脱俗的洁净。不同之处则在于:杨是热切里裹着冷静,张却在冷酷里和着热情。所以,看杨绛写字做人如同在雪楼里听雪落——之于张,则好比在艳阳下看花开。 同样气度,两种滋味。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我们仨》是哭哭笑笑中读完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情节,皆是关于钱锺书的。放下这书,钱的《围城》和《谈艺录》,拾来又看了一遍。落到眼里,尽是作者的好处——他真是温暖啊!却又如此犀利。市井小事,义理典故,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剥掉了层道貌岸然的壳,变得清晰单纯起来。钱锺书使我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世上,活得混沌也好,聪明也罢,都可以轻松快慰,是件好玩儿的事情。 我喜爱轻盈简易,自然爱化繁为简的人。然而,想要我讲述对钱锺书的热爱,却是羞涩难言。用文字来形容,是没有出路的。他在那里,活着死了,都在那里——笑着写着,他在哪里,都是一座山。而我,也是不得不匍匐在山脚下的。如此卑微鄙薄,却也如此欣喜。我爱他如同朝圣,平凡的内心容不下这样丰盈喜悦的情感,那感情泼到山脚下,也是平凡的,是我捧不起捡不起的一点私恋。 作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学问家,怎么可以像爱一个作家那样爱他?作为一个睿智机敏的作家,怎么可以像爱一个男性那么爱他?作为一个历经荣辱沧桑的男性,怎么可以像爱一个孩子那么爱他?怎么可以呢? 然而,那个在族里被认为“疯、傻、憨、稚气、淘气”的孩子,不是他是谁呢?那个写尽了嚼一嘴俏皮淘气话的小人物,却面对生活笨拙委屈得手足无措的大男子,不是他是谁呢? 在中文系的日子,暖洋洋的午后,恃才傲物的古文老师随便讲点什么,都带点不够矜持的显摆,我对他教学从来提不起兴趣,然而这位年轻的讲师却总是在念完整节枯燥难懂的讲义后,扶扶镜框,讲一些有关钱锺书的轶闻趣事,整个课堂于是从这时起带了些清新趣味进来。我也总能在他开场那刻精准地结束午睡,缩到椅子里,半梦半醒地听他白话钱锺书。 他嘴里的钱锺书总免不了半人半神地张致,我便恰好可以用浑噩的神智迷信他嘴里的“神”,用清醒的意志辨认他嘴里的“人”。 听他洋洋洒洒累述钱的博闻强识,也听他滔滔不绝地数落钱的痴怪愚钝,最后照例要听他牵牵绊绊地讲到和钱锺书一点儿七扭八弯的关联——说来算是钱的徒孙哩!我常常这样面带微笑地边听,边继续对钱的忖度:这是怎样一个精彩的人阿,对名利毫无兴致,却遣得如此众多的才人学子,身前身后地为他绘彩飞金,树碑立传——人,便是这样成了神吧?
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杨绛在《我们仨》里这样写她梦里的钱锺书:“我们在后舱脱了鞋,轻轻走向床前。之间他紧抿着嘴唇,眼睛里还噙着些泪,脸上有一道泪痕……我摸摸他额上温度正常,就用他自己的手绢为他拭去眼泪,一面在他耳边轻唤‘锺书、锺书’……他立即睁开眼睛,眼睛睁得好大。没有了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皮双得很美……” 我多喜欢她眼中的他啊!落单的时候,他会委屈、孤独、噙着眼泪,他眼皮双得很美——她已经九十二岁了,她梦寐思服,她这样疼惜他,这样地爱,她的恋人是孩童还是老者,有什么关系呢?他是智慧还是笨拙,对她,又有什么计较呢?“没有了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皮双得很美。”读到这里,我年轻的心脏肿胀疼痛,如同看到她和她的爱情跋山涉水,哗啦啦哗啦啦地穿越大片稠密的时光,看到白发苍苍的她披荆斩棘,无比衰弱无比强大地拯救她的恋人。我只恨自己不够坚强,不能陪她梦醒,亦不敢拨开梦境的薄纱,我不能面对这样的女人——空谷寂寂,她双目空空,而他,早已远去。她已经老了吗?他在哪里啊?哪里有爱人的桃源呢?那些花儿呢?还开着吗? 我记起儿时背白居易的《长恨歌》:“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咿呀稚气的声音常诵出悲凉来。我那时单以为时世人心残酷冷漠,破坏佳话。直至见了钱杨这一对,才知道自然界更要冷得让人心疼,它客观博大地运作一切,叫剖竹为符的两个人彼此辨认,相濡以沫,与子偕老,把一个变成两个——却又冷静地带走生命,泯灭往事,把两个变回一个。天人永隔更像个诅咒,它撮合宿世姻缘,给人无限遐思,再理直气壮地抹煞掉完满的结尾,留下余恨叫人来饮。于是,死的一半幻灭,活的一半伤逝!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 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 已经难辨真假 如今这里荒草丛生 没有了鲜花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 的春秋和冬夏 写着这些文字,我反复给自己放着朴树的《那些花儿》,和着旋律把歌词用黑体字一行行地穿插在文章里。一面只觉得妥帖体己,省了不少心思。 我听朴树荒着嗓子唱啊唱的:“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她。啦……她还在开吗?啦……去呀!她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听着歌的末尾,他用女声的叹息唉、唉、唉地为这曲子打拍子——荒诞离散。 他其实写得比我好。 合上钱杨的文字,我多想为他们做些事情。那些花儿呢?那些日子呢?六月里的凌晨3:00,想开罐啤酒了。微醺的清晨,我开大音响,亲爱的…… 让那些花儿开起来吧,让她们舒展馥郁如同青春,让那些日子温暖起来吧,让她们清晰柔软如同花瓣。 宋静茹,1980年5月25日出生,双子星座。女,吉林人。网名了了。获奖作品《孩子》一文曾感动了无数同龄孩子,而今宋静茹已经大学毕业,毕业于南开大学。毕业前出版个人小说集《只爱陌生人》。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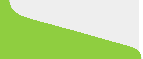 |
|
Y-zone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










